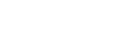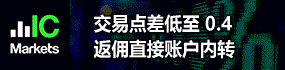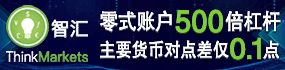[美文][转贴]如果想要了解美国.
<<論民主文集>>(1)
引言: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則
梅爾文?烏羅夫斯基 撰文
" ……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亞伯拉罕?林肯總統
1863年葛底斯堡演說
*****
在為保存美國國家完整而進行的大規模內戰期間,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國家公墓落成典禮上發表了一篇獻辭,他以一句鏗鏘有力的結束語,給我們留下了也許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家喻戶曉的關於民主的定義。他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之說 ,精闢地描述了民主政體的要素,可適用於一切有志締造民主社會的民族。
民主制度並非易事,它也許是所有政府模式當中最複雜最困難的一種。它充滿了各種較量和矛盾,必須有其成員兢兢業業的努力才能生效。民主制度不是為效率而是為責任明晰而設計的;民主政府可能比不上獨裁政權的行動快捷,但是它一旦投入行動,這種行動可以從民眾的支持中汲取豐富的源泉。民主制度,就其美國的表現形式而論,肯定不是一件終極成品,它在永遠不斷地演變。美國政府制度的外形兩個世紀以來沒有多大改變;但我們只要穿過表面,就可以發現巨大的變化。不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 ─ 而且他們也有道理這樣認為 ─ 他們的政體所依據的原則,直接源於1787年由制憲者所首次宣示的那些信念。
在這一批系列文章中,我們打算就其中某些原則的涵義加以闡明,略為介紹其歷史沿革,並且解釋一下,這些原則具體到對於美國政體的運作以及普遍到對於民主制度整體為何如此重要。鑒於任何一個民主政體都會不斷演進,這些文章也顯示出美國政體中的一些缺陷,以及美國如何對待這些問題。美國的模式固然在美國是成功的,但沒有任何人主張這是一切民主政體都必須遵循的模式。每一個民族都必須按照自己本身的文化和歷史來建立自己的政體。但是,我們這些文章列舉出若干必定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存在于民主制度中的根本原則。以如何制訂法律如何為例,具體方式可以千差萬別,但是無論採取何種方式,都必須依照一條原則,那就是公民應該參與這個過程,而且感覺到自己是這些法律的主人翁。
這些根本原則是什麼呢?我們列出了11條;我們認為,這些是瞭解民主制度如何發展演變以及在美國如何運作的關鍵。
憲政制度
法律的制訂必須有一定之規;制訂法律和修改法律必須採用已經得到共識的方法,某些領域 ─ 即個人權利 ─ 必須不受多數人的任意擺佈。憲法是一套法律,但它同時又遠比一套法律豐富得多。它是一個政體的建制典章,安排各個部門的權力並規定政府權力的界限。憲政制度的一個關鍵特徵,就是這個根本架構不能因一時多數人的意願而輕易被更動。要更動,就需要受治者明確無誤表示同意。在美國,自1787年以來,《憲法》只修正過27次。制憲者規定的程式使得修憲很不容易,但又並非不可能。歷次修正案大多是擴大了個人權利並消除了基於種族與性別的分野,從而延伸了民主。這些修正案沒有一次輕而易舉,但一旦通過,全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援。
民主選舉
一個政體,無論設計得多麼美妙,但除非主持這個政體的官員是由公民以有目共睹的對所有人一律公開而且公平的方式自由選出,否則,這個政體仍不能算是民主的。選舉的辦法可以多種多樣,但是所有民主社會都具有相同的根本實質:凡是具備資格的公民,都有權參加投票,個人應得到保護以免投票時受到不應有的左右,票數應得到公開公正的點算。鑒於大規模的投票往往容易發生錯誤和舞弊現象,因此,必須注意盡可能加以防止,這樣,萬一出現問題或是發生彼此得票接近的情況 ─ 例如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 人民也會理解,仍然可以承認選舉結果對他們有約束力。
聯邦制、州和地方政府
美國的聯邦政體是獨特的,權力由國家、州和地方政府分別承擔和行使。即使這個模式不適合其他國家,也仍有可資借鑒之處。政府同人民相隔越遠,它的效率就越差,受到的信任就越低。而美國人有了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就能夠在近距離觀察自己選出的一些官員。他們可以將政府的種種政策和方案同那些負責執行和實施的官員們直接掛鈎。而且,權力下放,就使得非法接管政府越發難以得逞。民主制度應該下放權力與職責,這條原則在一個幅員小而且比較整齊劃一的國度可能是無足輕重的,但是在一個幅員廣闊而且成份複雜的國度,卻可能是個重要的保障機制。
立法
按照歷史記載,人類正式制訂法律已有五千年之久,但是,不同的社會規範自己如何生活的方法卻是千差萬別,有的是由神王頒佈敕令,有的則是在村落集會上實行多數表決。在美國,法律是分多層次制訂的,從地方的城鎮委員會起,上至州議會,最終至美國國會。但是,在所有這些層次,都有公民直接或間接的廣泛投入。各立法機構都認識到自己要對選民負責,如果立法不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立法機構成員在下次選舉中就面臨敗北。民主立法的關鍵,並不在於其使用的機制或論壇,而是在於那種要對公民交代的責任感以及認識民意的必要性。
司法獨立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在1788-89年的《聯邦主義者文集》(The Federalist)中指出,法院既不掌握刀把,又不掌握錢財,本來是政體中"危險性最小"的一個分支。然而法院在民主制度中可以具有強大力量,而且在許多方面,法院是用以解釋和落實《憲法》約束力的機制。在美國,法院可以判定國會和州議會通過的法案同《憲法》相抵觸因而宣佈其無效,也可以因與此類似的理由禁止總統的作為。在美國,個人權利最有力的衛士就是法院體系;其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大多數法官是終身任職的,可以不受政治干擾,一心一意處理法案。儘管並非所有憲法法院都要一樣,但必須有一個機構擁有權威足以確定《憲法》到底是如何規定的以及政府各分支是否越權。
總統權力
凡是現代社會,都必須有一個能夠將各項施政職責付諸實施的行政首腦 ─ 從管理工作專案到指揮武裝部隊到戰時保家衛國。但是,在授予行政官履行職責的充份權力的同時,也必須限制他的權力,以防獨裁;這二者之間界線微妙,但必須劃清。在美國,《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規定了明確界限;雖然美國總統屬於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職務之一,但這個職務的力量來自受治者的贊同,也來自總統同政府其他分支進行良好合作的能力。在這裏,可以又一次看到,關鍵並不在於行政首腦職務如何具體安排,而是在於像 "分權制" 這樣的原則對總統職務施加何種約束。在民主制度下,當總統的,進行治理時必須依靠他或她自己的政治技巧,建立起一個同立法系統,尤其是同人民合作的框架。與此同時,公民必須感到放心,知道《憲法》的約束能保證總統或總理永遠是人民的僕人而非主人。
自由媒體的作用
同公眾的知情權緊密關聯的是自由媒體 ─ 即報紙、廣播和電視網 ,它們能調查和報導政府的運作情況,而不必害怕受到起訴。英國普通法曾規定,對國王提出任何批評 ( 類推包括對整個政府提出任何批評 ) ,都構成煽動誹謗罪。美國則終於廢除了這項罪名,並創造出一個新聞理論取而代之,這個理論對於民主制度大有裨益。在一個複雜的國家裏,一個公民個人很可能無法丟下工作去旁聽審判,或到立法機構去旁聽辯論,或是去研究政府的某項事務進行得如何。但是可以由新聞界來替公民代勞,通過報章雜誌與廣播電視將新聞界的所見所聞加以報導,讓公民按照所知資訊而採取行動。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依靠新聞界來查出腐敗行為,揭露司法的失職現象或是某一政府機構辦事的低效無能。任何國家,如果沒有自由的新聞事業,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任何獨裁制度都有一個標誌,那就是新聞界鴉雀無聲。
利益集團的作用
在18世紀,而且實際上直到19世紀相當一段時間,立法基本上是選民同他們選進國會或州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們之間的對話。由於當時人口較少,政府的施政專案較為有限,而且溝通較為簡便,公民就沒有必要成立仲介組織來協助他們轉達的自己的主張。但是到了20世紀,社會變得更為複雜,政府的作用擴大,選民要對許多事項說出自己的主張。公民為了在一些具體事項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成立遊說團體,即宣導某種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團體,以及一些專門關注特定事項的非政府組織。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這個現象,國內也有過不少非議,有些人指出,一些掌握大量錢財的利益集團能夠比另一些財力較薄弱的利益集團更有效地傳遞自己的聲音。這種非議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事實在於:有數以百計的這樣的團體在協助公眾和立法議員瞭解各種具體問題,這樣一來也就幫助了許多資財平平的公民個人能夠在一個複雜的時代讓議員瞭解到自己的看法。隨著我們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各種聲音會更多,而這些非政府組織對於公民們所關心的事宜,將會起有效的提煉與聚焦的作用。
公眾的知情權
在本世紀以前,人們如果想知道他們的政府行事如何,通常只消前往市政廳或是集市廣場去聆聽討論和辯論便足以。但是今天我們面對的是龐大複雜的政府機關,是往往厚達好幾百頁的規章法令,立法程式儘管要向人民交代負責,但仍然過於含混複雜,令得多數人難以明白究竟。在民主制度下,施政應該盡可能透明,也就是說,政府的審議和決策,都應該公之於眾,接受檢查。顯然,不是所有政府行動都應該公開,但是公民有權利知道,他們所繳納的稅款是如何開支的,司法部門是否有效率和效力,他們所選出的代表是否辦事負責。如何提供這些資訊,各個政體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是,任何民主政體,都不可能以封閉式運作。
保護少數權利
如果我們所說的"民主"是指多數的統治,那麼,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對待少數。我們所說的"少數",並不是指那些對獲勝的黨投過反對票的人們,而是指由於種族、宗教或民族原因而同大多數有無法消除的差異的人們。在美國,種族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為了解放黑奴,曾進行過一場流血的內戰,其後又過了一個世紀,有色人種才能夠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憲法權利。今天美國仍在努力解決種族平等問題。但這是民主制度的演變進化本性的一部份,這個制度致力於有更廣泛的包容性,要讓那些同多數人不同的人們不但得到保護免遭迫害,而且還享有作為全權平等公民的參與機會。有些國家以血腥恐怖的方式對待少數,事例不勝枚舉,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只不過是其中最為活生生的代表。然而,任何社會,如果一貫將特定的人群排斥在法律的全面保護之外,這個社會就不能稱其為民主社會。
軍隊受文職管轄
在古代,一個領袖的首要職責,是率領社會的軍事力量保衛國家或是征服他國。一個將領戰功彪炳,他的威望就十之八九會使他設法利用武力來把持政府;掌握了軍權的人,可以易如反掌地把別人統統趕下臺。在當代,一名上校或是一名將軍用軍力發動政變推翻文職政府的例子屢見不鮮。在民主制度下,軍隊不但必須處於文職當局的切實統轄下,而且還必須有一種強調軍人是社會公僕而非社會統治者的意識。這一點在有公民軍隊的環境中比較容易做到 ─ 所謂公民軍隊指的是,軍官來源於社會各界,服役期滿又返回到平民生活中。但是,原則仍然不變:軍隊永遠必須處於從屬地位;它的使命是保衛民主制度,而不是實行統治。
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推理出幾條貫穿性的原則。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民主制度下一切權力的根本來源是人民。美國《憲法》開宗明義毅然決然地宣佈了這一點:"我們,合眾國人民……茲制訂並確立本《憲法》。" 政府的一切權力必須來自人民,而且必須被人民認可為合法。認可手段可以有很多種,包括立法程式以及自由公平選舉。
第二條總體原則是必須分權,以免政府的任何一個部份權力大到可以違背民意的程度。雖然總統一向被視為美國政府中權力最大的職務,但是《憲法》對這些權力是施加限制的,要求行政首腦行事時必須同其他部門以及同選民群體保持協調。雖然軍隊受文職管轄的做法驟然看來似乎使得總統手中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但是,民主社會的軍隊特性阻礙濫用這一權力。何況還有法院,不但對行政部門施加制約,而且對立法部門也同樣施加制約。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必須有制衡,各分支都必須珍惜制衡的智慧和必要性。
第三,個人和少數的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多數不得使用自己的權力去剝奪任何人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制度下,這一點往往難以做到,尤其是每當人群成份複雜,對一些要害問題意見紛紜之時,就更為困難。但是,一旦政府剝奪了某一群人的權利,那麼,全體人民的權利也就陷入了危險。
這幾條原則貫穿了《論民主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而每篇文章的主題,又都在充實這些基本原則。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通過法律的制訂,通過能夠審視政府運作的新聞事業,以及通過能夠瞭解政府所作所為的知情權,人民的意願得到了保證。這些意願,通過各個利益集團而得到表現,儘管表現力的強弱略有不均。在美國,分權是《憲法》明文規定的,而《憲法》是一部美國人民幾乎奉若神明的建制典章。人民的意願,也表現為對政府的制約,表現為軍隊受文職管轄,表現為聯邦制。少數的權利,通過多種途徑得到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獨立。
但是,這些原則能不能轉換到別的文化裏去呢?對此並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任何政府制度是否成功,要取決於許許多多相互交錯的因素。在美國歷史上的殖民地時期,倫敦的帝國政府對鞭長莫及的美洲各個殖民地無法實行嚴密的控制,因而權力移到了當地的各個立法機構。隨後又產生了一個《憲法》中所體現的聯邦制度,反映出美國人民獨特的歷史處境。由於認為英國國王濫用權力,因此對行政權力給予限制;由於有了民間武裝的經驗,則為軍隊受文職管轄奠定了基礎。
個人權利來之比較不易,但是,隨著民主制度在美國演變發展,人民的權利從有產的白人男子擴大到包括一切種族、膚色和信仰的男男女女。多樣化原先被看作是政府所面臨的一道難題,結果卻成了民主制度的一個強大力量。在幅員廣闊的民主國家,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如果硬要推行整齊劃一的生活方式,那就非一敗塗地不可。美國人民不但不反對多樣化,而且把它當作自己民主信念的一塊基石。
其他國家在進行民主實驗時 ─ 民主永遠是一種實驗,將需要研究怎樣才能將這些文章中所闡述的那些特徵在自己本國的文化中最完美地建立起來並保持下去。不存在什麼獨一無二的道路;借用詩人華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話說,民主就是眾多,常常自相矛盾。不過,我們只要著眼於那些不變的根本原則,即根本權力在民、政府權力必須受制約、個人權利必須受保護,那麼,可以有很多達到目標的途徑。
---------------------
作者介紹:
本系列編輯梅爾文?烏羅夫斯基(Melvin I. Urofsky)是弗吉尼亞州大學歷史與公共政策學教授,曾撰寫編輯過40多本書。他的最新作品是《沃倫法院》(2001年) 以及同保羅?芬刻爾曼合著的《一次自由的進軍:美國憲法史》(第二版,2001年)。
15楼
《論民主文集》(2)
憲政:美國及其它
葛列格?羅素 撰文
" 在有政府的環境中,人的自由的含義是,生活中有穩定的、適於社會
所有成員的法律可依,且法律是由該社會確立的立法權力機構所制訂。 "
─ 約翰?洛克
《政府論(下集) 第四章》(Second Treatise,Ch.4)
****************
憲政,或者說法治,意味著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是有限的,並且這些限制可以通過成文的程式得到實施。作為一套政治或法律思想,憲政指的是,政府既為社會全體謀利益,也維護個人的權利。
根植于自由政治思想的立憲政府最早起源於西歐和美國,目的是捍衛個人的生命和財產權、捍衛宗教和言論自由。為了保障這些權利,制憲者強調對政府每個分支進行制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不倚的法庭、以及政教分離。這一思想傳統的代表人物包括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法學家愛德華?柯克(Edward Coke)和威廉?布萊克斯通(Wiliam Blackstone)、政治家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艾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21世紀的憲政問題很可能產生于看起來是民主制的政府。"非自由民主政體"(illiberal democracies)是現代歷史的一個現象,這種政體之所以能獲得合法性從而有勢力,是因為這些政權似乎還算民主。非自由民主政體 ─ 也就是不具有憲法保護的自由的名義民主政體 ─ 不僅是不完整的民主,而且是危險的,因為伴隨它而產生的是侵蝕自由,濫用權力,民族分裂,乃至戰爭。民主在世界上的傳播並不總是伴隨相應的憲法對自由的保護。不少民主當選的領導人利用他們的權力來為限制自由尋找根據。富有活力的政治自由傳統並不僅限於自由公正的選舉,或擴大政治表達機會。自由的民主還提供了政體分權的法律基礎,從而捍衛言論、集會、信仰和財產權等基本自由。
憲政:歷史基礎
現代自由政治理論在建立立憲政府的鬥爭中得到實際表述。自由主義的最早、很可能是最偉大的勝利是在英格蘭。曾經在16世紀支持都鐸王朝的新興商人階層領導了17世紀的革命,成功地建立了議會、最終是議會下院的最高權力。現代憲政最突出的特點並不在於國王必須服從法律 (雖然這一觀念是所有憲政的重要特徵);國王必須服從法律的觀念在中世紀就已經形成。現代憲政的突出特點在於建立有效的實施法治的政治機制。現代憲政產生於一個政治前提,那就是,代議制政府有賴於公民的贊同。
另外,現代立憲政府是和經濟與錢袋的力量密切相聯的,宗旨是,政府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因而納稅人必須在政府中有代言人。一方提供財力,另一方解決不滿,這種相輔相成的原則是現代立憲政府的關鍵。國王封建制稅收的減少、代議制體制以及民族團結的增強,而不是對國王和宮廷的象徵性效忠,都促使真正有效地限制了王權。
但是,正如我們從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English Bill of Rights)的條款中可以看到的那樣,英國革命為之而戰的並不僅僅是保護狹義上的財產權,而是要建立起自由人士所認為的為人類尊嚴和道德境界所必不可少的自由權。英國的《權利法案》中所列舉的 "人的權利" 逐漸弘揚到英國之外,特別是反映在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18世紀,美國和法國建立了立憲政府,19世紀,這一趨勢成功地在不同程度上擴展到了德國、義大利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國家。
憲政與美國國父的精神遺產
美國社會的憲法秩序建立在自由和有理性的男女公民的共識之上。這是以 "社會契約"(scoial contract)為象徵所表達的一種為一定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信任。"社會契約" 理論的最盛行時期是17和18世紀的歐洲,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這些思想家們認為,出於個人的自我利益和理性,個人對社會應該負有政治義務。他們認識到使個人既享有權利也承擔義務的文明社會的長處,也認識到假想中完全沒有政府權威的 "自然狀態" 的缺陷。"社會契約" 的思想反映了一種基本意識,那就是,如果要讓一個自由政府得以存在,如果要確保人類不淪為狂熱激情的犧牲品 ─ 激情統治所帶來的是混亂、暴政、反理性秩序的叛逆,就絕不能僅靠建立政府,而是必須建立起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2篇(Federalist No.2)中指出,如果要政府具備起碼的權力來保障社會的共同利益,個人就要把某些自然權利讓予社會。其結果是,公民作為立憲民主的參與人,肩負著服從法律和在公共事務上服從社會決定的責任,即使在自己有截然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亞里斯多德和斯賓諾莎都認為,不管是虛無主義惡徒或無政府主義者這樣的 "野蠻人"("beast-man"),還是一手操縱法律、會成為獨裁者的 "神人"("god-man"),都必須得到控制或者從社會中清除出去。霍布斯、洛克以及美國開國前輩也都這樣認為。這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前提,少之,文明社會無法存在。立憲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不僅在範圍上有限度,不僅需要基於共同意願,而且還必須為社會整體、為社會中的每個人謀福利。
縱觀美國歷史,從1776年的《獨立宣言》、1781年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1787年制定《憲法》(Constitution),一直到1791年通過《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不管是革命先驅還是《憲法》制定人,都繼承了上述思想。美國為自由和憲政而進行的鬥爭體現在下列幾個主題中。
人民主權
"我們人民……制定這一《憲法》。" 美國《憲法》"前言"(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中所包含的這句話表達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或曰民治的思想。《憲法》起草人撰寫了這樣一份治國大綱,並交給人民批准。他們的主導思想是,終極政治權力既不在政府手裏,也不在任何一位政府官員手裏,而是在人民手中。"我們人民" 擁有我們的政府,不過,在我們這樣一個代表制的民主體制中,我們把日常行政權交給一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機構。但是,這樣做絕不會以任何方式損害或者減少人民的最高權利和責任。政府的合理性依賴於被管理的人,他們保持著不可剝奪的和平更換政府或修改《憲法》的權利。
法治
但是憲法理論認為,政府必須做到公正與合理,這不僅是出於多數人的意願,而且也符合更超然的規律,即《獨立宣言》所指的 "自然法則與造物之神"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1766年英國議會頒佈的《公告》(Declaratory Act),聲明對美國殖民地擁有主權,"在任何一切事務上" 都對殖民地具有約束力。這個《公告》生動反映出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的差異。法治意味著仰仗更高層次的 ─ 超然和為人類所共同理解的 ─ 法則與正義,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人為的或由當代政治家施行的法律。美國的立國前輩相信,法治是美國社會秩序和基本公民自由的命脈。法治的含義在於,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受到一套相對公正的法律的制約,而不是由一批人的意志左右,那麼,受專制和獨裁統治之害的機會就要小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所包含的政治義務並不只適用於臣民或者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而且也適用于君主和當權者。通過既不讓個人也不讓國家淩駕於最高法律之上,制憲者給個人權利和自由建立了一層保護。
權力分離以及制約平衡體制
一個國家只能通過人來治理,如何建立一個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是美國國父必須回答的問題。畢竟,這些領導人是一批政治現實主義者,力圖把憲政精神融於他們所在的時代和環境。詹姆斯?麥迪森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1篇(Federalist No.51)中也許最好地表達了這一理念與實際運作的矛盾。麥迪森宣稱,野心必須用野心來抵消。人的利益必須牢牢地和他所在之地的憲法權利交織在一起。只要對人性稍有瞭解就知道,"這一機制為控制政府濫用權力所必需。" 如果天下男女猶如天使一般,那麼,既不需要從內、也不需要從外對政府進行制約。但是麥迪森是一個現實的人。用他的話說,憲政意味著一個方針: "通過反對派和有相反利益的人來顯示良好動機下的缺陷。" 一個對人有著謹慎的尊重的憲法架構,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由其管轄的人。但是同樣重要的是,要在政府內部建立謹慎的制約平衡機制。
通過把政府的職能分散在三個獨立的分支中,制憲人確保立法、行政和司法這三種政府的主要權能不會被任何一個分支所壟斷。把政府權威分配在三個互不相干的分支中,也防止聯邦政府過於強大以至使州政府變得無能為力。制憲人有意使政府的權力和責任重疊。例子之一是,國會雖具有制訂法律的權力,但這一權力可以通過總統享有的否決權得到制約。反過來,總統的否決又可以被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推翻。總統是軍隊的總司令,但只有國會才有權組成和補給軍隊,也只有國會才能正式宣戰。總統有權任命所有聯邦法官、駐外大使和其他政府高層官員,但所有任命必須得到參議院的審查和批准。任何法律都必須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通過才能生效。
最高法院具有判斷立法和行政分支的行為是否違憲的終審權力。1803年的馬伯裏訴麥迪森案,奠定了美國聯邦司法部門的司法審查權。司法審查權並非來自於《憲法》的明文規定,《憲法》中沒有明確提到這一權力,而是來自於一系列法庭案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這些案件的共同點是 ─ 至少就司法權威的觀念倫理根據而言,它們反映了司法審查與超然法則之間的聯繫。當年的美國人也一定會贊成這一古老的學說,即如果成文法、或者說人為制訂的法律與自然法則相違背,那麼,人為的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是對法律的曲解。詹姆斯?奧提斯(James Otis)在1764年的《伸張和得到證明的英國殖民地權利》(Rights of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中道出了這一思想。他寫道:
"自然法則不是人造出來的,也不是人能夠修改或者改變的。人要麼履行和維護這一法律,要麼違背或打破這一法律。但這後一種行為從來都不是沒有懲罰的,懲罰甚至就顯現在此生中 ─ 如果懲罰意味著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墮落,看到自己由於愚蠢和邪惡而從正派人墮落為卑賤之徒,或者看到自己從國家的朋友、也許是先父變成貪婪的虎豹的話。"
邦聯制
美國的奠基人還決定,權力也必須在不同級別的政府,即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得到劃分。由於1781年到1787年間的《邦聯條例》沒有能夠為美國殖民地創立一個可行政府,因此出席1787年在費城舉行的憲法會議的代表給予中央政府更大的權力。《邦聯條例》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由大陸會議初建的政府和美國《憲法》1787年創立的政府之間,發揮了一種橋樑作用。殖民地人民對在英國中央政府專橫統治下的經歷記憶猶新,因此,《邦聯條例》的起草人有意要建立一個由擁有主權的州組成的"邦聯"("confederation")。但是《邦聯條例》沒有給予國會向各州徵募資金或軍隊的權力,政府的效力到1786年便已經瓦解。
根據美國《憲法》,邦聯制將讓位於聯邦制,在聯邦制下,權力將由國家政府和多個州政府分享。國家政府在一定的領域將擁有至高權力,但是州政府將不是從屬中央政府的下級行政單位。州的權利通過幾種方式受到保護。首先,《憲法第十修正案》明確規定,一些領域的活動由州政府自行處理。例如,州政府基本上自行制訂本州的預算,負責制訂和實施許多對本州居民有影響的領域中的法律。第二,每個州在美國參議院的代表性受到保障:每個州不管面積大小,都有兩位參議員。第三,負責正式選舉美國總統的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由州選舉出來的選舉人組成,每個州至少有三名選舉人。第四,修憲程式本身也反映了州的利益,因為要對《憲法》進行任何修改,必須獲得四分之三州議會的同意以及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票的贊同。這些保護措施包含在《憲法》內,防止大州左右小州。在對制約平衡體制的全面設計中,州政府與國家政府分享權力是其中又一種結構性的制約。
爭取個人權利的鬥爭
美國《憲法》前言展望了一種新的、基於如下原則的美國政治秩序:建立一個更完美的聯邦,提供共同防禦,建立司法公正,保障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自由福祉。在甚至更早的時候,《獨立宣言》就已經提到了作為人,人人生來具有的"不可剝奪"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取消的權利。但是不論過去和現在,不同黨派對如何保障公正和自由的福祉,一直存在著尖銳分歧。最初起草並交給各州批准的美國《憲法》,並沒有包含任何關於個人權利的條文。對這一異常現象的一種解釋是,《憲法》起草人認為,鑒於新建國家政府的權力已經如此嚴格地受到限制,並不需要對個人權利作額外保護。此外,其他聯邦主義人士指出,列舉額外的權利會帶來額外的不利,也就是說,一些根本的、然而沒有被具體指出的權利,將很容易受到政府的侵犯。
雖然反聯邦制的人在1787年起草《憲法》的鬥爭中失敗,但是他們還是迫使對手做出了一些讓步。由於擔心新的國家政府權力過大,他們要求《憲法》明文寫清楚對個人權利的一系列保護條款。他們還在一些州議會取得了聯邦黨派領袖的承諾,贊成對《憲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一些州要求確保通過一個權利法案,否則他們將不批准《憲法》。聯邦主義人士兌現了他們的諾言。1789年,美國第一屆國會通過了《憲法》的頭十個修正案。到1791年,由這十個修正案組成的《權利法案》獲得了必需數量的州的批准。此外,聯邦主義人士本來擔心,專門提出保護某種權利會危及到對其他沒有被專門提到的權利的保護,但是由於第九修正案明確了對《憲法》中未予具體描述的基本權利的保護,這一顧慮得以被打消。
《權利法案》限制政府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個人自由的侵犯。《權利法案》還禁止國會就 "建立" 任何正式宗教而立法,也就是說,不許使任何一種宗教具有優於其他宗教的地位。《權利法案》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內容旨在保護被懷疑或者被指控犯罪的人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正當法律程式、公正審判、有權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言和供詞,有權不受殘酷和非常的懲罰,不可因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告。《權利法案》最初通過的時候,只適用於國家政府的行為。
限制州政府侵犯公民自由權是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1865年)、《第十四條修正案》(1868年)和《第十五條修正案》(1870年)的主要內容,這些法案也被稱為《重建法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它們在美國內戰後獲得通過,旨在消除奴隸制。過去100年期間,《憲法》前十條修正案所規定的自由權都被納入第十四條修正案,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州可以剝奪其公民正當法律程式或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自20年代以來,《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尤其在解決公共政策的難題上扮演了越來越活躍和重要的作用,這些問題涉及從學校祈禱、檢查吸毒的硬性規定是否合乎《憲法》,到生育控制和死刑等等。 "公正" 、 "自由權" 這些根本原則以及 "正當程式" 和 "受法律同等保護" 等憲法原則被一代又一代人賦予新的意義。這些常常是通過抗議運動和非暴力反抗而取得的進步,反映了過去200年來人性感悟程度與社會道德的變化。
《權利法案》確立了某些不能被大多數人左右的自由權,它所基於的理念是,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將削弱他們的公民地位,實際上也就是他們的人格。《權利法案》和《憲法》所保證的一系列的廣泛權利形成了自由政府的內涵。公民權利可以直接來自于自然權利,也可以非直接地來自一個建立在由憲法、習慣法先例以及成文法形成的共識基礎上的社會所做出的政治安排。麥迪森及其同事在憲法會議和第一屆國會上的成功體現在,他們創建了一套自我調整的程式和結構,使之能夠合法保護權利,並且建立起在美國實踐的標準。
憲政、自由和新世界秩序
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和其東歐共產主義同盟國的崩潰,帶來了人們對自由民主思想和立憲政府的勝利感和對其前景的樂觀。2000年12月,在世界範圍內促進民主的非營利組織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公佈了一個大型研究報告,詳細羅列當今世界上191個國家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權的現狀。這一題為《2000-2001年世界自由狀況》(Freedom in the World 2000-2001)的研究顯示,十年以來朝更加自由的方向日益積極發展的趨勢,在2000年裏得到繼續。根據這個組織的年度調查,86個國家、25億人口(也就是40.7%的世界人口)被列為有 "自由"。這是該調查有史以來最高的比例。這些國家的居民享受廣泛的權利。59個國家、1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8%)被認為 "部份自由"。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在這些國家比較有限,這些國家的特點常常是腐敗、由執政黨控制,在一些國家還存在種族或者宗教衝突。調查認為,47個國家、22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5%)屬於 "不自由" 類型。這些國家的人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
"自由之家" 的調查更加深了一個普遍的信念,那就是,除了民主政體外,再沒有其他更可取的選擇;民主已經成為現代化的固定支柱。但是,後冷戰成就中的另一特徵,卻給決策人和政治思想家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和困難。民主當選的政府 ─ 往往是通過公民投票而連任或者得到肯定的政府,經常無視憲法對他們的權力限制,剝奪其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從世界許多地區,我們看到了國際生活中出現的這一令人不安的現象,即:沒有自由的民主。
這一現象的核心在於民主與立憲政府的差異。這個問題一直很難被意識到,因為在西方,至少一個世紀以來,民主恰好與自由民主並行。但是從理論上來說,與憲政自由主義相關的一系列自由權與民主並不是一回事。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時代起,民主一直意味著人民主事。不同的學者,從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到約瑟夫?順彼得(Joseph Schumpeter),到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都對民主是選擇政府程式的這一觀點做過表述。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解釋了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開放、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是民主的本質,是民主必須具備的條件。但是,選舉所產生的政府有可能是低效、腐敗、沒有遠見、不負責任的政府,受特別利益集團的支配,無法採納為公眾謀利的政策。這樣的政府雖然不是人們想要的政府,但是卻不是非民主的政府。民主是一項社會美德,但是卻不是唯一的社會美德,要理解民主和其他社會美德與缺陷的關係,就要把民主和其他政治體制的特點區分開來。選舉和民眾參與並不總是能確保產生一個自由的立憲政府。人們對多黨制選舉在整個南歐和中歐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迅速傳播越來越感到不安,其原因恐怕就是因為選舉後出現的現象。一些很受民眾歡迎的當選領導人逾越議會,依靠頒佈總統令執政,破壞了憲政的基本運作。
沒有自由的民主自然也有各種各樣。有的程度較輕,有的則接近於暴政。在拉丁美洲,許多民主政體經歷了過去十年惡劣的經濟狀況,仍然生存下來,沒有受到來自軍方或反政體的政黨的明顯挑戰。但是這些民主政體中的大多數還有待鞏固。一些國家在正式的民主結構相當虛弱的情況下堅持了下來。但是,沒有憲政自由作後盾,民主就不能得到完整的鞏固。除了贊同權力競爭的原則,還必須對權力的使用給予根本和自行的限制。過於強調純粹的民主、把它作為對自由的終極檢驗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不去努力為這些過渡中的國家建立富有遠見的憲法。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靠的不只是經常舉行選舉,或寫下一串權利;必須建立一個不會踐踏這些權利的體制。立憲政府著眼的不僅僅是選擇政府的程式,而且是建立起多項不受大眾激情左右的審議機制,從而捍衛個人自由和法治。這就要求精英階層共同努力,調動憲法的協調機制,利用相應的政治建制,常常也通過精英階層之間做出協議和安排,也就是,政府通過在主要政治黨派和利益集團之間建立聯盟來維持穩定。其目標是,無論哪個政黨或者哪個派系掌控國家,國家權力都得到限制。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要讓世界安全以便發展民主。21世紀的挑戰或許是,要讓民主穩健以使其發展到全世界。
相關讀物:
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Edward D. Corwin, 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99)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Harbison Belz Kelly, et al., ed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7th ed., W. W. Norton, 1997)
Theodore Lowi and Benjamin Ginsberg, American Government (6th ed., W. W. Norton, 2000)
Charles H. McIlwai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Macmillan, 1932) Ellis Sandoz, A Government Of Laws: Political Theory,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作者介紹:
葛列格?羅素(Greg Russell)是奧克拉荷馬大學諾曼分校副教授,政治學系研究生部主任。他的著述有:《漢斯?J?莫根陶與美國的治國倫理》、《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外交的公共美德》以及《調和內在之權利與外在之不當:武器和思想在戰爭中的力量》。他還在政治哲學、美國外交史以及國際關係領域發表過文章。羅素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有關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治國方略的書稿。
7楼
論民主文集》(3)
民主選舉的原則
小D. 格里爾?斯蒂芬森 撰文
"每一政治憲法的目的都在於...首先確立執政者,
即具有洞察時務的最高智慧和追求社會公共目標的最佳品德的人。"
─ 詹姆斯?麥迪森
《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7篇(Federalist No.57)
****************
1776年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指出,"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管理者的共同意願",這句話道出了民主理論的核心。87年後,當美國由於11個州拒絕接受1860年的選舉而爆發內戰時,林肯總統重申了共同意願的原則,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管用什麼字眼表達,這一立國原則都要求有一個選舉體制,即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1788年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1篇(Federalist No.51)中所說的作為"以人民作為對政府的首要控制力"的原則。
選舉通過以和平方式確定當權人並使其具有決策合法性,得以解決任何政治體系所面對的一些關鍵問題;如果一種選舉制度的特徵有助於人們普遍認識到選舉的自由公正性,那麼這些目標就更容易達到。促使人們認識到選舉的公正自由性的因素包括:普及性而不是排斥性的選舉權資格和投票機會;選票份量同等而不是力量有別;選舉結果根據預先建立的規則確定,投票和計票中的舞弊欺騙被壓縮到最低程度。這些自由公正選舉的標準在美國政治歷史上並非一成未變;其變化過程反映了每一代人在努力理解參政群體的性質、合法異見自由度、代議、選舉結構與行政管理等問題時的經歷。
誰可以參加選舉
《憲法》第一條第二節規定,人們只要有投票選舉"州議會人數最多一院"的資格,就有資格投票選舉美國眾議院的一名成員。《憲法》除了為國家職位確立一定的資格條件外,讓每個州自行規定選民資格。根據幾個州的法律,這意味著選舉權在一開始的時候,只限於擁有一定數額的財產或納一定數額的稅金的白人成年男子。到1830年,財產限制基本上被取消,男性白人都獲得了選舉權。
在美國內戰前,黑人一般不能投票,即使在禁止奴隸制的州也是如此。1865年內戰結束時,《憲法》的三個修正案預示了美國參政群體、也就是誰有權投票和參選權的觀念的重大變化。1865年通過的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1868年通過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宣佈,"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于合眾國並受合眾國管轄的人,都是國家公民以及其所居住州的公民", 首次為國家與州公民提供了一個憲法定義。這一修正案還確定,"任何一州都不能拒絕給予其管轄內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護。" 1870年通過的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取消將種族作為衡量投票資格的標準,但是這一諾言歷經幾十年未能兌現。
實際上,一些州自行採用了一些方式來回避《憲法》要求。其中一個被稱為"祖父條款"的規定直到1915年才被最高法院取締。根據這條規定,凡是1866年1月或者之前投過票的人以及他們的直系後代可以不參加投票資格文化測驗。這一規定基本上使得每個黑人都必須參加當地舉行的可能難以通過的文化測驗。比"祖父條款"沿襲更長的是白人初選。初選是一個政黨內部選舉該党候選人的選舉,即由選舉團而不是僅僅由政黨領導人選擇候選人,20世紀初,美國許多地區都實行這樣的初選,以使政黨民主化。在由一黨占支配地位的州,如在民主黨為主的南方州,初選實際上就成了正式的選舉,因為在真正的大選中,共和黨人的反對勢力充其量只能是象徵性的,或者根本不存在。所以,雖然黑人在大選中可以投票,但是一些州禁止他們在初選中投票,消除了他們對當地或者州選舉的影響力。直到1944年,最高法院才明確規定,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所保證的投票權既適用於大選,也適用於初選。
即使如此,在上世紀進入60年代之際,在南方,每四個黑人合格選民中只有一人登記,而選舉時黑人實際的投票率還要大大低於這個比例。但是60年代中兩條戰線上的行動導致這種情形在十年內出現重大變化,使黑人的投票率達到與白人投票率旗鼓相當的程度。首先是成功地取消了有礙窮人、特別是黑人投票的人頭稅。1964年通過的憲法《第二十四條修正案》禁止在聯邦選舉中使用人頭稅,兩年後,最高法院廢除了把人頭稅作為州選舉條件的規定。另外,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也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選民的最重要立法,基本上剷除了阻止非洲後裔美國人投票的一些更微妙的做法。由於實行了聯邦政府監督選舉以及禁止文化水準測驗,黑人選民的登記人數到1967年在佐治亞州翻了一番,在阿拉巴馬州翻了幾乎三番,在密西西比州躍升了幾乎800%。
相形之下,1840年代就開始的婦女選舉權運動花了更長的時間才為婦女贏得正式投票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一經確立,無需進一步的立法維護。1869年,懷俄明領土成為美國第一個允許婦女投票的地區,但是其他地區的跟進非常緩慢,特別是由於1875年最高法院裁決,州可以繼續禁止婦女投票而不會違反《第十四條修正案》。到19世紀末,又有另外三個州允許婦女投票。在1920年大選前不久,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才賦予全國各地婦女投票權。
誰可以競選公職
參政群體所包含的另一個含義涉及擔任公職的權利,這方面的有關規定是對兩種對立價值的平衡。一方面,州在傳統上更傾向於少限制,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人符合年齡、居住和公民資格,這個人就有權爭取讓自己的名字上選票,以供投票人選擇。《憲法》一貫禁止把宗教作為國家公職的一個標準,最高法院1961年的裁決也禁止州一級這樣做。
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多數州也盡力阻止太多的候選人和太多的政黨參選。由於不同的政黨代表和協調不同的利益,因此美國政治傳統更喜歡由一個黨內聯合陣線組成的多數派統治,而不是由不同政黨之間的聯合陣線的多數統治。這種傾向性是為了形成一種體制,以便更有可能使選舉得勝者贏得大多數選票或者至少差額較大的多數票。這種目標在候選人和政黨眾多的情況下比較難以實現。
這一目標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實現:想參加競選的人必須參加一個黨的初選,為自己的請願書收集一定數量的簽名 (同時繳納一筆立案費)。州一級的公職所需的簽名數量以及立案費比較高,地方公職所需要的簽名數量以及立案費相對要低得多。同樣,一個政黨要想讓其候選人的名字出現在選名榜上,也許需要稍微顯示一些證據,說明對該候選人原已存在的支持 ─ 不管是以請願書上的簽名還是以該候選人在已往選舉中獲得的選票數量為憑均可。
有關上州候選榜的規定,給任何希望競選總統的"第三黨"(除共和黨和民主黨外的任何政黨)候選人形成特別的負擔。不管是競選聯邦、州還是地方公職,候選人的名字若要出現在所在州的選名榜上,候選人必須符合在每個州的參選資格。這對民主黨與共和黨這兩個主要黨來說十分容易做到,但是對第三黨卻會是一個可畏的挑戰。
儘管美國歷史幾乎一直由民主或共和兩大政黨主導,但是選民的選擇並不象乍看上去那麼局限。這裏至少有三個原因:政黨自身的主張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第三党使主要政黨意識到選民觀點的變化;任何由國會或總統的行政部門實施的政策隨時會受到最高法院對其合法性的挑戰。
合法異見自由度
沒有選擇的選舉是毫無意義的選舉。明智選擇的一個必要條件是,那些反對執政者的公民享有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對政策提出批評、和召集組織支持者的權利。如果有關官員有權壓制反對派的聲音,那麼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美國通常給予不同意見很大的自由度,但是一些顯著的例外情形說明,有時在最需要自由的時候,自由反而面臨最大的危險。在一些人看來,在美國歷史的某些時期,共和國的安全似乎有賴於遏制反對意見和大逆不道的觀點。1798年通過並實行了三年的《鎮壓叛亂法》(Sedition Act)規定,誹謗總統或國會是犯罪行為。1950年代冷戰時期實行的《史密斯法》(Smith Act)規定,主張推翻政府是犯罪行為。
相反,另外一些人認為,自由是維護安全的最佳途徑。這種觀點為美國開國先賢所崇尚,在美國許多的法庭裁決中占上風。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1943年寫道,"與人意見相左的自由不僅僅限於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果真如此的話,這樣的自由充其量只能算是自由的影子。對其實質的考驗在於,在觸及現行秩序核心的問題上是否有意見相左的自由。"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小威廉姆?J?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 Jr.)在1964年提出,有關公共問題的辯論"應該沒有任何顧忌,充滿活力,廣泛敞開,...甚至可以包括對政府以及官員的激烈、尖刻、有時難聽刺耳的攻擊。"總之,政府雖然可以在面臨即將爆發的暴力時限制煽動性的言論,但是根據《憲法》規定,如今沒有所謂的非法思想一說。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1927年宣稱,"如果需要通過討論暴露虛假和謬見,通過教育防止邪惡的話,那麼方法就是更多言論,而不是壓制聲音。"
代表制
選舉的結果是選出為人民謀利益的官員。在美國,官員和百姓的聯繫最清楚地反映在州議會以及美國國會的組成上,從事立法的議員代表整個州或者州裏的一個地區,即選區。州以及聯邦所實行的代表制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到權力的地理分佈,而且影響到權力在相互衝突的利益團體之間的分佈。例如,在國會,《憲法》規定每個州有兩名參議員代表,而每個州在眾議院的代表人數則由人口數量決定。因此,居民人數不到50萬人的懷俄明州在參議院得到的代表和將近3400萬人口的加利福尼亞州得到的代表程度是一樣的。但是在眾議院,懷俄明州只有一個代表,加利福尼亞州根據2000年人口統計的數字有53個代表。這項在1787年憲法會議上達成的折衷方案,使得小州能夠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否則,如果完全按照人口確定代表人數,小州的作用會變得微不足道。
州議會負責為他們自己以及為本州的聯邦眾議院代表劃分選區。美國各州基本上都傾向於一個選區一個代表的做法,即如果一個州有十個眾議員名額,那麼州議會就把該州劃分為十個區,一個區選一個代表。
相對於人口比例制和某些一區多代表制,一區一代表制抑制了第三黨的發展,也許還會大大減少一個規模較大的政治少數派的影響力。這是因為如何劃分選區可以加強或者減弱一組選民勢力或者一個政黨的力量,這種劃分方式被稱為格裏蠑螈(gerrymander)。(這個詞是由格裏"Gerry"和蠑螈"salamander"兩個字結合而成的。埃爾布裏奇?格裏[Elbridge Gerry]是1812年時麻塞諸塞州的州長,他主持重新劃分了該州的參議員選區,新選區的形狀據說很像蠑螈。) 如果一個州劃分選區到了極不公正的地步,並且持續多年,最高法院有可能裁決其違反《憲法》;但是只要沒到這種地步,這種做法已經在美國政治中屬於約定俗成。儘管如此,一個黨在力圖通過劃分選區線取得優勢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服從一定的規則。選區的劃分不能看上去象主觀意志的產物,選區應該是整塊相連的。不過,美國每整數十年進行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年的選舉尤其重要:因為控制州議會的那個黨在新十年開始的時候為州議會以及國會選舉劃分選區,這一劃分將在新的人口普查結果產生之前的十年中有效。
但是,最高法院很早以前就廢除了另一種導致代表性相當不平等的選區劃分方法。在50年代以前,州議會和國會選舉選區的明顯數字不平等幾乎在每個州都很常見。人們在不斷從農場搬遷到城市,從城市搬遷到郊區,但是選區劃分跟不上變化。一些人口稀疏的鄉村地區比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得到更多的代表。顯然,在任的議員不會急於把自己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選出局。
最高法院在6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裁決廢除了這樣的選區劃分法,要求所有選區的劃分以一人一票為基礎,也就是,一個選區的人口必須等於該州人口除以選區數。到60年代結束前,最高法院對美國的議員代表性做了革命性的改變,把政治權力從鄉村地區轉移到城市地區,特別是城郊地區。這樣做的結果是,人口多數能夠選舉立法機構中的多數。
選舉結構與程式
選舉的規則與做法既可以使人感到自由與公正,也可以帶來相反的效果。讓我們以投票障礙、計票、競選資金規定等幾方面為例。
美國選舉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很多人不投票 (在美國投票屬於自願,而不象在有些國家屬於法律要求)。即使在很引人注目的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率近年來也僅僅徘徊在50%左右,也就是說,有整整一半的合格選民(幾乎所有17歲以上的公民)不去投票。這與1960年總統選舉時達到的65%的現代高投票率相距甚遠。1996年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只有49%,獲選連任的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贏得了49%的普選票,也就是說,他是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選民選出的總統。
造成這一趨勢的因素包括:選民的公民與社會義務感下降;選民認為投不投票對他們的生活沒有影響,因而莫不關心;雙職工家庭比例上升也可能會減少前往投票站的人數;另外,處於繁榮和平時期的人們,不感到大選中有重大利害悠關的問題。
另外必須瞭解的一點是,在美國,投票意味著做出三個不同的決定。除了決定去投票、投誰的票外,選民還必須先登記才能投票。這一要求乍一看來好像妨礙投票,因為選民登記通常在投票前幾個星期就截止了。此外,由於登記按州進行,州內按縣進行,縣內按選區組織,那些剛剛搬到一個新地方的人,幾乎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登記或者把他們原來的登記轉到新的選區。鑒於美國人口流動性大,這意味著總有一定數量的選民因為沒有登記而無法參加投票。把選民登記系統簡便到象申請或延長駕車執照那樣(也就是所謂的"司機選民"設想)是否有助於提高投票率,還不得而知。
在完整統計選票方面,多年來美國建立了法律保障措施,儘量減少錯誤,確保公正。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州都有法律,允許在一些情況下重新計票,允許表面看來失利的候選人挑戰選舉結果。不然的話,人們對計票是否準確產生的懷疑也許會損害對選舉公正性的信心,降低當選人的合法性。2000年的總統選舉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次拖延甚久的選舉清楚地顯示了通常平凡單調的計票過程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總統選舉投票
根據《憲法》規定,每個州被給予和該州國會代表人數相等的選舉人選票,1961年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三條修正案》給予首都哥倫比亞特區三張選舉人選票。贏得全部538張選舉人選票多數票(至少270票)的候選人贏得總統選舉。各州選舉人12月18號在州府開會投票(故稱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憲法》規定,各州選舉團選舉人"以由各州議會規定的方式任命產生。"從19世紀中至今,各州的總統選舉人都由各州居民投票選出。除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外,美國其他48個州都實行贏者囊括全部選票的做法,也就是,在一個州得票最多的總統候選人得到該州的全部選舉團選票,從而有效地避免其他候選人分得選舉團選票。
即使在許多美國人眼裏,選舉團制度好像也太為過時了。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佛羅里達州在11月7號選舉日後之所以成為決定勝負的州,主要就是選舉團制度所致。佛羅里達州的總統選舉從11月爭執到12月是因為,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和民主黨候選人阿爾伯特?戈爾(Albert Gore)在該州得到的普選票十分接近。在其他49個州,布希和戈爾獲得的選舉團選票勢均力敵,沒有佛羅里達州的25票,誰也達不到270張選舉團選票。所以,贏得佛羅里達州普選的候選人將贏得該州的選舉團選票,從而成為美國第43屆總統。雖然人人都知道戈爾在全國範圍內獲得的普選票比布希多幾十萬張,但是這一差距不起任何作用。決定總統選舉結果的是佛羅里達州的投票。
佛羅里達州的大多數選票是由機器閱讀和統計的。但是,一些使用打孔票的選民不是沒有把孔打透,就是打透了但是打下去的那一小塊紙沒有完全脫離選票,再麼就是打得太輕、只留下一個印,因此機器將這些選票歸為不合格選票。還有一些選民乾脆沒有投總統的票。佛羅里達州在其他選舉中也曾發生過同樣的事,但是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去處理過,因為在那些選舉中沒有發生過選票如此接近的情況,後果也沒有這麼重大。戈爾在佛羅里達州選民投下的600萬張票中僅落後布希幾百票。他和他的支持者希望每個選區的選舉官員對被機器拒讀的選票進行人工統計。布希及其支持者擔心,通過人工計票決定選民的意圖會使得計票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觀影響,從而使他不公正地落選。在布希看來,計票機不會偏向哪個候選人,而人工計票卻會因事關重大而受到影響。在這場計票爭議下,兩位候選人的立足點是共同的:他們都堅持公正計票。他們的分歧在於如何做到公正計票。
最高法院最終在12月中做出裁決:要進行人工計票,就必須依照一套統一標準來決定選民的意圖。當時離選舉團投票日只差幾天,最高法院因此得出結論:限於時間關係,不可能進行合乎憲法的人工計票。不然的話,一個選民的選票可能得到與另一個選民的選票不同的對待,因而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美國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所帶來的影響將遠遠不止于2000年總統選舉。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將成為美國未來任何政治選舉中指導重新計票的原則。從現在起,只有根據統一標準、在確保平等對待、儘量排除主觀性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重新計票。
對競選支出的限制
2000年選舉另外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它突顯了金錢在拉選票過程中的作用。據說共和黨策略人士馬克?漢娜一百多年前曾經說過,"政治中有兩樣重要的東西。第一是錢,我記不得第二是什麼。"為了防止腐敗或者避免腐敗之嫌,《聯邦競選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在1974年的修正案中對競選資金的來源、數額以及使用作了重大限制。不過這些限制觸及到了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因為錢在政治中相當於代言人:候選人、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必須通過錢來發展壯大他們的組織,通過媒體向選民傳遞他們的主張。
為了部份維持這一錯綜複雜的法令,最高法院1976年就競選捐款與競選開銷作了一個重要的憲法區分。由於法院認為與限制競選開銷相比,限制競選捐款對言論的危害較小,由於競選捐款為腐敗或腐敗之嫌開路的可能性較大,所以最高法院廢除了限制競選開銷的條款,但是維持了對競選捐款的限制。另外,最高法院還維持了一個有條件的由公共資金資助總統選舉的做法:在初選和黨代會上,聯邦政府向符合條件的候選人提供與他籌集到的資金相等金額的資金;在大選中則向候選人提供一筆數額有明文規定的競選資金。作為交換,候選人統一遵守一定的開銷限制。這樣做的部份目的在於,拉平主要政黨候選人之間的資金水準。《聯邦競選法》對以上所謂的"硬錢"("hard money")進行了制約,但是對於用於黨組織發展、拉票宣傳、以及圍繞競選主題而進行的媒體閃電戰的捐款(也就是"軟錢","soft money"),並沒有做任何規定和限制。
一個穩定的民主過程
自由公正的選舉是保證"被管理者的共同意願"這一民主政治基石的關鍵所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使權力與合法性同時誕生,而不公正與不誠實的選舉則會使人們對聲稱當選的人產生懷疑,從而大大削弱其當政能力。
很少有人認為美國的選舉政治是完美的。它的一些特徵有時妨礙、轉變、壓制或者歪曲了人民的共同意願。但是出於幾個原因,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的選舉系統總的來說是公正而誠實的。首先,大約150年前導致美國內戰的衝突就是美國選舉程式之效力的一個明顯說明:通過決定勝者和敗者,選舉達到了選舉預定的目標。失利的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雖然不一定是高興地、但卻是情願地接受得勝的候選人,承認其治國權。這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是以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為先決條件,在這個體制中,根本的價值觀和利益很少受到威脅,也許永遠不會受到威脅。
第二,選舉的頻繁程度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政黨、一個黨內沒有任何一個派系能夠保證永久掌權。今天的多數明天也許會被另一個很不同的多數所取代。這是民主理論的一個要點:多數派處於不斷變換之中。第三,由於這一選舉體制保護競爭的權利,所以多數派可能是暫時的。一個選舉如果不給予真正的反對派任何機會的話,那麼這個選舉就是騙局。
最後,美國選舉把選民與公職掌權人聯繫在一起。後者必須得到多數選民的贊同才能掌權。因此,人民視當選官員為由人們授權的代理人,代表他們行事。美國的選舉使得公職官員成為人民的僕人,而不是使人民成為政府的僕人。
無論人們如何衡量美國在民主政治上的進步,其他國家還是有可能會選擇不在所有方面模仿美國的模式。美國選舉政治的一些特徵完全是由歷史造成的。美國若是在21世紀走上建國之路的話,則不會通過選舉團選舉總統,可能也不會保持各州在參議院席位的平均。另一些特徵,如新聞自由、普選產生國會議員等,則毫無疑問會保留下來。但是,不管怎麼說,從美國民主歷程中所顯示的一些特徵,很可能是世界其他地方維護穩定民主進程的根本。
首先,應該普及投票權,並且使選民能夠方便地投票,使所有選票的實力相等。基於性別、政治信仰、民族或宗教原因而對參政群體實行限制,將有損於政權的合法性。相反,普及選舉權促使社會的所有成員認識到自己在已有秩序中的利益,因為每個成員都有最終實現願望的機會。
第二,鼓勵更多的選民參加投票應該是選舉的重要目標之一。低投票率即使不引起警覺,也應該受到關注。低投票率不僅會導致出現官員在沒有多數合格選民支援的情況下當選,而且還會使一些善於組織、有強烈動機的利益集團的影響力變得過於強大。
第三,高度的政治言論自由對民主過程十分重要。對合法的政治異見進行限制會窒息反對者的聲音,抑制選舉政治;壓制不同觀點有可能會迫使持不同政見者從合法的參政管道轉向暴力途徑的抗議。
第四,選舉和代表制必須使得大多數人民能夠控制政府,但是與此同時,也必須防備多數人壓倒和吞沒少數群體。在另一方面,反映選民的多數意願是一個立法的根本因素,立法機構必須有效地反應多數人的意願,如果讓少數人的利益在選舉中佔有過大的份量將動搖這一根本。一旦讓少數人的觀點取代多數人的觀點或導致決策過程陷入僵局,那麼政府將失去行動能力。
第五,鑒於只有在多數人認為選舉公正而自由的情況下,選舉才能產生效果,因此,必須建立適當的程式,一旦出現投票不公的指控,迅速做出反應。沒有這樣的補救措施,選舉政治很快就會被認為是一場騙局。
最後,在一個大多數人口在最重大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的社會,可能難以保持選舉的自由公正。有時候,一個政治體制是否健康是可以通過沒有被列入競選大綱的問題和從來沒有出現在選票上的提案來判斷。
伍德羅?威爾遜一百多年前指出,"民主建制永無完結之日。它們如同活組織一樣,總是處於成長過程中。過自由人民的生活是一件費力的事。"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少不了要對選舉進行嚴格的審視,做出可能的改變。認識到一個選舉體制的缺陷與欣賞它的益處同樣重要。
相關讀物:
Mark E. Bush, Does Redistricting Make a Difference? Partisan Representation and Electoral Behavio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chette Gaylord Chute, The First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Right to Vote in America, 1619-1850 (Button, 1969)
William Gillette, The Right to Vote: Politics and Passage of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5)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nt, eds.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gathon Press, 1986)
Alexander Keysse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ic Books, 2000)
Harold Porter Kirk, A History of Suff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MS Press, 1971)
Donald W. Rogers, ed. Voting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Democracy: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Voting and Voting Rights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
作者介紹:
小D. 格里爾?斯蒂芬森(D. Grier Stephenson Jr.)是福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的政府專業教授。他教授的課程包括美國政治、最高法院以及《憲法》。他的著述有《競選和法庭:美國最高法院在總統選舉中的作為》、《美國憲法:引介文章與案例選析》(與阿爾菲厄斯?湯瑪斯?梅森合著)。
眾人皆醒我獨醉
8楼
《論民主文集》(4)
聯邦制與民主
大衛?J?博登哈默 撰文
"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事實上不過是人民的不同的代理人和
委託人,被賦予不同的權力,不同的職責。 "
─ 詹姆斯?麥迪森
《聯邦主義者文集》第46篇(Federalist No.46)
****************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歷史上最勢均力敵 ─ 也最令人困惑 ─ 的一次選舉。在選民投票結束一個月以後,才最後確定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當選美國第43屆總統。在這一個月期間,在全世界的注視下,佛羅里達州的選票之爭在地方法庭、州法庭和聯邦法庭間幾度上下,最後是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導致定下結果。令許多外國觀察人士不解的是,為什麼美國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的投票標準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地方官員在全國選舉中為什麼會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
美國公民或許也對州與州選舉程式上的差別之大感到意外;但是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間的交叉互動卻算不上罕見。美國的普通人幾乎三天兩頭都會與三層政府的法律與行動打交道。區域劃分、交通控制、衛生、教育管理、街道整修等數不清的服務,主要都是由得到州政府授權的地方政府進行的。州政府基本上控制著教育政策、刑事司法、商務和職業規章、公共衛生等一系列其他的重要領域。而國家政府的行動 ─ 從國防到外交,從經濟與貨幣政策到社會福利改革 ─ 因其影響廣泛,也成為全國各地新聞中的日常內容。
很少會有人意識到,無論是2000年總統選舉這場大戲,還是不計其數的日常生活小劇碼,它們的表演場地同是200多年前由美國《憲法》締造人搭造的大舞臺。作為生活在殖民地的人,美國的開國之父對遙遠的大英帝國政府施加的權威感到不滿,認為中央集權是對他們的權利和自由的威脅。因此,1787年在費城召開的憲法會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在給予中央政府充份權力以保護國家利益的同時,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國家與州兩級政府分權是當時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這一分權系統,也就是聯邦制,如今被廣泛認為不僅是美國對政府理論的獨特貢獻,而且是美國立憲制的卓越之處。
聯邦制的定義
聯邦制是兩個或多個分享權力的政府對同一地理區域及其人口行使權力的體制。迄今為止,一元化政府體制仍然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政府形式。這一體制只有一個權力來源,即中央或國家政府。儘管在聯邦制和一元化政府體制下,民主都可以發展壯大,但是這兩種形式的政府體制具有重大和實質性的區別。例如,英國是一個一元化政府。英國的議會對英國國內發生的一切事情擁有最後決定權。即使議會將地方事務的權力下放,也仍就可以命令英國的任何城鎮和縣郡做議會認為應該做的事;只要議會願意,議會甚至可以廢除或改變任何城鎮或縣郡的界限。
在美國,情形很不一樣。坐落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家政府的法律適用於任何生活在美國境內的人,但是美國五十個州的各州法律只適用于該州居民。根據美國《憲法》,國會無權廢除一個州,也沒有任何一個州可以僭越只有國家政府才可以行使的權力。事實上,在美國所實行的聯邦制下,美國憲法是國家政府和州政府的權威所在。反過來,憲法也反映了美國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是民主政體中的最高權力所在。
在一個聯邦制國家,國家政府有明確的權利,對對外事務有完全的主權。但是,在國內事務上如何行使權力,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根據憲法,美國政府在管理州際和對外貿易、造幣、移民歸化、維持陸軍部隊或者海軍部隊等事務上,擁有非其莫屬的權力。美國聯邦制保證每個州政府都是共和政府,從而保證沒有任何州能夠建立其他政體,比如說,君主制。在上述這些領域,國家利益顯然超越各州利益,因而在這些領域的權力也相應地歸屬國家政府。國家政府還具有解決兩州或多州爭端、解決不同州公民之間爭端的司法權。
但是,在國內政策的其他領域,國家政府和州政府可能會有平行或者重疊的利益與需要。在這些領域,州政府與國家政府也許會同時行使權力;在這些並存權力中,最主要的是徵稅權。在《憲法》沒有就國家政府權威做出規定的領域,州政府可以在不與國家政府可合法行使的權力相衝突的情況下採取行動。在一些影響公民日常生活的重大問題上,如教育、罪行與懲罰、健康與安全等,《憲法》沒有做出直接的責任劃分。根據美國開國前輩所依據的共和原則,特別是約翰?洛克的理論,人民應該擁有這些權力,通過不同的州憲法,人民將這些權力委託給州政府。
《憲法》締造者認識到聯邦與州這兩級政府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特別是在並行使用權力的領域,於是採納了幾種策略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使美國《憲法》具有高於州憲法的地位,並得以通過聯邦法庭貫徹之。《憲法》中的一個條款規定,如果國家政府行使的憲法權力與州政府的合法行動發生衝突,那麼國家的權力至上。《憲法》還明確禁止州政府行使某些授予國家政府的權力。《憲法》締造者當時為了爭取使《憲法》獲得通過,同意支持旨在阻止國家干預個人自由權的《權利法案》,也就是《憲法》的前十個修正案。通過羅列州與州之間的相互義務,《憲法》為州與州的關係奠定了基本原則,並使得任何新加入聯邦的州與最早組成聯邦的州地位平等。最後一點是,通過給予各州在美國參議院、也就是國會上院,同等數量的議員席位,各州在國家政府得到平等代表。美國立國之父力圖通過所有上述方式,減少聯邦數層政府間的矛盾。
創建美國式聯邦制所依據的是一個新的主權,或曰最高統治權,觀念。在英國和歐洲的政治理論中,主權是一元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1776年美國從英國獨立以前存在的帝國危機中,殖民地人提出,雖然英國議會控制帝國的整體事務,但是在實際中,各殖民地的立法機構制訂了自己的法律。不過,儘管如此,獨立戰爭時期的早期美國政府仍然是按照主權不可分割的舊觀念運作的。根據1783年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也就是美國的第一個憲法,每個州或每個前殖民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各州之間僅僅通過一種 "友好同盟" 關係來處理國家問題。然而,這種邦聯制政府在實踐中不盡人意,甚至在一些人看來,是危險的。有些州不僅剝奪它們的一些公民的自由權,而且還常常在損害國家整體利益的情況下謀求自己的利益。對《邦聯條例》的廣泛不滿導致1787年召開憲法會議,起草新憲法。
憲法會議產生的《憲法》以下列著名詞語開宗明義:"我們,合眾國人民……",從而顯示出新國家的主權所在。這個由人民創立的《憲法》,既沒有把主權交給國家,也沒有把它交給州政府。曾經看來不合邏輯的政府套政府的模式,在新《憲法》下成為可能,因為國家和州政府的權力都是由擁有主權的人民授予。這一授權是以書面《憲法》的形式表達出來,給不同層次的政府劃分出各自的角色。州與國家政府之所以可以對同一地域、同一人口同時行使權力,是因為它們的著重點不同:州著重於地方事務,國家著重於更廣泛的問題。美國試驗的政府形式是,讓州與國家政府作為互不相關的獨立實體並存,各自具有自己的許可權範圍;其道理在於,兩級政府同是為了服務於民。
一個演化的典型
聯邦制在美國運轉得如何呢?對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聯邦制這種政府形式事實上一直是一個動態架構,這一特點非常適合美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在過去200年的歷史中,美國聯邦制下的權力劃分在法律上和實踐中都發生了多次變遷。美國《憲法》是一份很靈活的檔,旨在使國家能夠適應情況的變化。在有些情況下,《憲法》修正案給予了國家和州政府有異於最初設想的權力;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法庭對這些權力又做出了不同的詮釋。國家和州政府的權力平衡是否得當,是美國政治中一個不斷引起辯論的問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1913-1920年)的觀察是,這個問題"無法由哪一代人的觀點解決"。他說,社會與經濟的變化、政治價值觀的變化,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 ─ 所有這些都要求每一代人把聯邦制當作 "一個新問題" 來對待。
即使粗略地看一下美國《憲法》就可以感覺到,在影響日常生活的事務上,國家政府只有很少的功能。在美國歷史的最初一百年,情形一直是這樣;影響公民生活的事務幾乎都是由州政府決定。州政府規定所有的罪行與刑罰,建立合同法,制訂公共衛生和安全規章,制訂有關教育、福利和道德的法律標準。
儘管州政府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在美國內戰(1861-1865年)以前,人們辯論的最迫切的公共政策問題之一,仍然國家權力的範圍。大多數人認為國家權力應該受到限制,但是,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不斷把聯邦制推到政治辯論的中心。對中央集權的畏懼而導致的美國獨立戰爭的影響仍然很大,憲法會議和制憲辯論中所遺留下的模糊之處,也令人三思。《憲法》的語言很寬泛,沒有就在許可權分配給國家政府後,州政府是否保留剩餘權力做出明確規定。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在實際中,當時的州政府很有能力圓滿行使政府職能,而後來的情形是,有越來越的事務需要通過多州協調才能解決。
圍繞奴隸制問題進行的美國內戰,解決了聯邦的性質以及聯邦政府的最高權力問題。1868年通過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包含一些允許合法擴大國家權力的詞句,但是,內戰並沒有解決圍繞國家和州政府之間許可權分配的所有問題。不過,這一辯論的歷史環境發生了變化。在19世紀後半葉,美國成為一個製造大國,隨之出現了國內的大市場、大城市,財富集中以及嚴重的社會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大企業對產品和服務的壟斷,引起人們對無拘束的經濟勢力的恐懼。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不受控制的經濟勢力與不受控制的政府權力一樣可怕。
沒有一個州或者幾個州的聯合體能夠有效地確立一種環境,既刺激又控制商業增長及其後果。所以,國家政府 ─ 此時已經越來越經常地被稱為聯邦政府 ─ 開始以 "州際商務貿易" 條款為依據,擔當起這一責任。《憲法》給予國會的權力中包括 "管理對外商務以及州際商務" 。到1887年,國會依據管理州際商務的權力制訂了針對壟斷的聯邦法律。在不到20年內,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對從全國彩票、烈酒貿易到食品和藥品工業的多項內容,做出了周詳的規定。
儘管這一立法的大部份內容旨在防止州政府干預工業的增長,但其結果是,使國家權力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時代,延伸到原來被認為是州政府責任範圍的醫療和福利領域。世紀之交時,以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年)為首的的進取派人士,對聯邦政府的這種權力延伸毫不感到躊躇,他們認為,州政府需要聯邦政府的幫助來履行其職責。最高法院 ─ 此時其詮釋《憲法》的最高權威已經得到承認 ─ 雖然接受並推動這一目標,但仍然力求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不過,大趨勢已經明瞭:聯邦權力隨著國家需要的增加而增加,州權力則相應縮小。
20世紀30年代,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所實行的新政(New Deal)經濟計畫要求為對應大蕭條經濟危機,給予聯邦政府更大權力。這向保守的州與聯邦利益的平衡關係發出了進一步挑戰。國會通過的措施為聯邦政府管理福利(創建社會福利體制)、農業、最低工資以及勞資關係等鋪平的道路;同時,另外一些法律允許針對諸如交通、通信以及銀行與金融等重要領域制訂聯邦法律。伴隨著救濟項目和多種社會實驗項目,新政計畫締造了一個國家行政體制,二次世界大戰和其後的冷戰更加強了這一體制。這個過程堪稱是一場憲法革命:聯邦政府現在開始在諸如勞資法或銀行規則等以前幾乎完全由州政府行使權力的領域,行使權力。
國家在聯邦系統內的作用在20世紀後半葉繼續擴大。最高法院推翻了通行的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詮釋 ─ 這種詮釋對聯邦政府的許可權範圍定義狹窄,並且擴大了聯邦政府在刑罰、社會福利、種族關係以及法律平等保護等領域的監管權。到上個世紀末,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不為聯邦權力所及。這一效果也許最明顯地表現在人們申明自己公民身份時的說法。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份時期,相當多的公民首先把自己視為所在州的公民;到了20世紀末,人們更多地視自己為聯邦公民。
聯邦制革命並沒有終止關於如何恰當分配州與聯邦政府權力的辯論。圍繞州與國家政府應當在聯邦系統內承擔什麼角色的分歧,仍然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內問題都涉及到哪一層政府有權制訂或貫徹有關該問題的政策的矛盾。區分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功能也不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當前的聯邦系統在對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做出回應時,往往不分彼此、責任相容。
分權的優越性
如今,在學者們稱之為的合作聯邦制內,權力決策被共同分擔。這一點在美國已經根深蒂固,即使在兩級政府發生矛盾的時候也不例外。例如,在1960年代,南方州一方面拒絕按照聯邦政府的要求實行種族融合,另一方面在建造州際公路系統的問題上予以合作。合作聯邦制之所以成為可能,在於幾個運作程式,其中包括分擔成本、聯邦指導方針以及共同管理。國會同意部份支付那些符合聯邦利益、但是主要使一個州或者一個地區的居民受惠的專案。這些專案包括公路、廢水處理廠、機場以及其他改善州或地方基礎設施的工程。聯邦政府在給這些專案撥款的同時提出一套指導方針,州政府必須採納和貫徹這些指導方針才能得到撥款。例如,出於對醉酒駕車的關注,國會最近把聯邦公路撥款與州交通法降低血液酒精度標準掛鈎。最後,州與地方官員是通過自己設計的專案、通過自己的部門來貫徹聯邦政策。職業再培訓就是這樣的一個專案,每個州設計並管理一個由聯邦出資的培訓專案,滿足該州居民的特別需要。
美國聯邦制的經歷能給其他地方的民主政府提供什麼經驗教訓呢?聯邦政府並不是常見的政府形式,大多數國家採納中央集權的一元化政府。另外,議會政體的經歷也表明,實行民主並不一定要以聯邦制為前提。但是,聯邦制的原則對任何地方的民主政府都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權和政策與政治下放。
美國人歷來認為,中央集權對自由權構成威脅,傳統上,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受置於遙遠的中央政府的權力。如何給予政府必要的權力、但又防止形成危害自由的中央集權是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權力授予兩級政府,使得每一級政府各自在其範圍內具有最高權力。最接近人民的州政府事實上起著制約國家政府的作用。這一創新在美國立國前輩看來很有道理;事實上,美國的代表制要求代表與被代表的人民有地域上的直接聯繫。地方觀念對現代人來說仍然具有吸引力,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人們本能地 "更喜歡在自己身邊、為自己所熟悉的東西,不放心遙遠而抽象的東西。" 分配給州的權力常常被稱為 "州權", "州權"觀念基於的前提是,地方觀念是重要的,人們願意信任他們有能力控制的政府。和國家政府相比,人民本能地感到州政府能夠滿足這一要求。這種信念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希望地方政府控制那些影響他們每天生活的建制,如員警、學校和醫院等,但同時堅持,公民權應該全國一致,而不應該因州而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聯邦制都在限制權力的框架下,滿足了地方和國家的需要。
聯邦制通過政策和政治下放,能夠滿足解決地方問題的需要,有助於民主。美國是一個地域遼闊複雜的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同的種族、民族和宗教把不同的文化和道德價值帶到社會、經濟和政治中。如果沒有有利於表達分歧和滿足不同需要的機制,對這樣一個國家實行民主管理會困難得多。在同一個問題上,州與州之間可以採納差距很大的政策,從而使公民可以選擇生活在一個政策適合自己的道德與文化價值的州裏。以賭博為例,有的州允許,有的州禁止。每個州通過州法律,實行適合該州大多數公民的需要、經歷和價值的政策。在賭博問題上,各州做法不同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實行統一政策所需要的全國共識。
當然,公共政策上的多樣化做法並不是完美無缺。對公民的根本權利和利益絕對不應打折扣。例如,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不應因地而異。做法的多樣化還有可能導致待遇不平等,比如,一個較窮的州無法象較富的州那樣為教育等類基本項目提供資金。但是,聯邦系統的一個寶貴特徵就是,人們有可能嘗試除基本權利外的不同的處理問題方式。
州,常被稱作民主化的實驗室,這是很有道理的。從社會福利到教育改革,從健康到安全規章,在這些領域的創新一次又一次地首先來自州政府。早在國家採取行動前,一些州就進行了種種改革,如:廢除奴隸制,把投票權擴大到婦女、非洲裔美國人以及18歲的公民,直選產生國會參議員,等等。在上述這些問題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形成共識的時候,這些州一級的行動擴大了民主化的前景。在這一意義上,州同時充當著政治改革者與仲介者的角色,提供了新思想的試驗場,幫助在州和國家的多數人中間形成可行的折衷途徑。
聯邦系統還能擴大人們對政治與政府的參與。政府層次越多,投票的次數就越多,擔任公職的機會就越大。州與地方政府選舉數千公職人員,而全國選舉只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兩名官員。(從法律上來說,這兩個職位不由選民直接選出,而是由每州選民選出的選舉團成員投票選出,但總統選舉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全國選舉)。許多州與地方公職是未來國家領導人的訓練場。例如,在美國的上五屆總統中,只有喬治?布希(George Bush, 1989-1993年)不曾在州一級擔任公職。卡特(Carter)總統、雷根(Reagan)總統、克林頓總統以及現任總統喬治?W?布希都首先在各自的州當選公職。雖然絕大多數州或地方公職人員最終並不會擔任聯邦一級的職務,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從中學習到政府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的作用,這些寶貴經驗會從根本上加強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社會也從中得益,因為這樣一來,能夠擔任更高職務的合格人材也相對更多。
多層政府還能夠增加非公職人員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無法在某一級政府施加影響的利益團體,也許會讓另一級政府聽到它們的聲音。在1950和1960年代,民權宣導者在反對種族融合的南方州面臨強烈反對,但是他們為種族平等而進行的努力在聯邦政府中獲得支持。20世紀初,主張建立勞工和環境法的人常常在州議會獲得成功,但是卻在國家一級受到挫折。因此,聯邦制使得政府更有可能對各州相互不同、有時相互競爭的經濟與社會利益做出反應,從而有助於鼓勵和管理一個大型共和國內的健康的民主多元化。詹姆斯?麥迪森和其他《憲法》締造者一道,非常看重多種利益組織並存的局面,因為這種局面能夠防止形成有可能踐踏少數人權利的永久的多數派。
最後,聯邦制提供一個可以有力批評和反對政府政策和行動的舞臺,從而強化民主。一個在聯邦失去權力的政黨仍然有可能贏得州與地方職位,因而能夠挑戰聯邦政府的決定或重點。雖然這類的反對有些不免純粹是黨派性的,但是大部份無疑表達了對某一政策或某種做法是否明智的真正保留意見。因此,公民所享有的反對被他們認為是不正確的國家政策的自由,在聯邦制中得到保護。這種方式宣導對政府進行有效和必要的批評,從而使民主得到加強。
富於創造性的較量
兩百多年來,聯邦制為美國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架構。聯邦政府所聲稱擁有的權力與州政府所聲稱擁有的權力總是在相互較量,這種較量今天仍然存在。要減少較量就要始終注意政府的角色,不斷評估這兩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是否得當。這一不斷變化中的平衡 ─ 它往往富於創造性 ─ 依據的是人民主權的原則,所以說,聯邦制引起的爭論焦點在於,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哪一個最能夠充份地表達人民的意願。這些爭論也關係到哪些價值觀將在政治思想的競爭中占上風。對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最後答案,聯邦制固有的內在較量永遠不會消失。
不同層次政府間的較量也許在實際中顯得混亂,但是美國人發現,除他們自己的警惕和守護之外,這種較量或許是對他們的自由權的最好保障。美國的立國先輩無疑是這樣希望的。詹姆斯?麥迪森1792年寫道:"如果這種改良的自由政府理論沒有在實施過程中遭到玷污,那麼,它將也許成為立法人給國家創下的最佳業績,給世界提供的最佳經驗。" 一個國家倘若希望尋求一種最能促進自由的政府形式,那麼,聯邦制提供了一個值得考慮的榜樣。
相關讀物: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Penguin, 1987)
Michael Les Benedict,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 Concis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6)
Daniel J. Elazar, American Federalism: The View from the States (3rd ed., Harper & Row, 1984)
Daniel J. Elazar, Exploring Federalism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7)
Jack P. Greene, Peripheries and Cent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xtended Polit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7-1788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Michael Lienesch, New Order of the Ages: Tim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aul C. Nagl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The Union in Americ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eter Onuf, 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James T. Patterson, The New Deal and the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J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Vintage Books, 1997)
---------------------
作者介紹:
大衛?博登哈默(David J. Bodenhamer)是位於印弟安納波里斯的印第安那大學-普渡大學歷史教授兼波利斯中心執行主任。他撰寫編輯過六本著作,包括:《公平審判:美國歷史上被指控者的權利》(1992),《權利法案在200年後的現代美國》(1993,與小詹姆斯?W?艾利合著)。
12楼
《論民主文集》(5)
民主社會的立法
戈登?莫利斯?巴肯 撰文
"任何一個時期的法律內容都大致與當時被認為適宜的條件相應;
但是它的形式和機能以及它達到理想結果的程度,則多半取決於歷史。"
─ 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
《普通法》(The Common Law),1881年
****************
從殖民地時期起,美國人就開始制訂法律,並且為維護一個有良好規則的社會至今仍在這樣做。雖然制訂法律的具體程式在200多年中不斷發展,但是民主立法的特徵依舊:要得到人民的贊同,要有一個制約與平衡體制,要有公共政策上的靈活性使之適用於當時當地的問題。
在17和18世紀的美國,人們派代表參加殖民地大會,制訂管理日常經濟與社會關係所需要的規則。哪里應該修路、應該怎樣給公共滋擾行為下定義,都可以通過辯論而決定。道路促進商業,農業廢物處理不單單是一個美學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一個有良好管理的社會的健康。
19世紀,人們聚集到密蘇裏,就大蓬車管理制訂規章。這些"路規"的目的在於保證美國人在長途跋涉幾千英里到太平洋海岸的路途中免遭危險。 淘金者在到達加利福尼亞金礦、離開了車隊後,又就如何劃分淘金區制訂規則。這些淘金者希望建立一個有良好規則的社會,來保護他們的生意,使之得以繁榮。
在21世紀的加利福尼亞,仍然有鄰里共同修改規章的做法,他們在正式的社區公約的範圍內,修改具體居民社區內有關房產狀況、規矩和房屋改造許可的規定。這些房產主人有權制訂所需的規則,以便大家有章可循。不管是在小城鎮的市政廳還是在首府大樓內,不管是在邊區定居點還是在都市豪華的起居室,財產擁有人、公民以及一切追求美國夢的人都參與了涉及社會經濟關係的立法。這一傳統貫穿於美國地方、州和聯邦的立法機制中。
美國法律傳統的起源
這種日常立法程式是從英國歷史中沿襲下來的做法。英國殖民者把他們的立法傳統帶到美國殖民地以後,針對新環境在實施中做出了一些修改。英國國王授予不同殖民地的業主和聯合股分公司一些不同程度的立法權,不過,無論是否有這些立法特權,所有英國殖民者已經都有法律可循,即古老的憲法,或者說世人所知的"英國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這一法律防止政府侵犯英國人的權利。普通法中包括《大憲章》(Magna Charta),也就是約翰國王(King John)1215年簽署的憲章。《大憲章》保障合理的法律程式,財產權,以及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這一古老的英國法律的關鍵核心在於私人財產與自由之間的關係。自從14世紀以來,私人土地財產得到了積極的法律保護和定義,但是英國歷史以及美國殖民地的經歷使美國人清楚地感到,必須在主權人民贊同的情況下,才能夠對財產權以及行使個人自由的權利做出更動。
政府的合法性基於其管理物件的贊同這一理念,起源於古代希臘和羅馬,歐洲現代早期的政治理論家大量充實了最高統治權在於人民的觀念。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殖民者通過加強專門給予人民的權利、進一步限制政府的許可權範圍而推進了這一思想。這些專屬人民的權利後來被寫進州與聯邦的人權法案中。如何防止政府因濫用主權人民所賦予的權力而踐踏人權,是美國憲法會議所面臨的問題。來自州和聯邦的代表以立法形式創立了內部的制約與平衡體制。政府的每個分支都將在立法中具有獨立性,但是它們的權力相互重疊,從而限制政府在體制內的影響力,提供更廣泛的民眾參與機會。
擴大法律涵蓋面
在美國歷史不同時期,民眾參與政府的廣泛程度有所不同。在建國初期,只有白種男性財產擁有人能夠參加投票,能夠擔任立法職位。到了19世紀,有產人才有投票權和擔任公職權的規定逐步被取消。但是婦女、非洲奴隸、美洲印第安人和亞裔仍然長年被排除在立法程式之外。要求平等的運動在19世紀開始發展,到20世紀取得成果。婦女從地方上組織起來,向立法議員要求權利。她們加入了反奴隸制的社會勢力,1848年在塞尼加福爾斯(Seneca Falls)宣佈男女平等,並向西部發展,而且在西部發現更加肥沃的爭取權利的政治土壤。在懷俄明和猶他這兩個還沒有正式加入聯邦的准州,婦女在1869年和1870年分別贏得了投票權。在加利福尼亞,婦女通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法律習俗在1849年贏得了社區財產權,但是直到1911年才贏得投票權。在全國範圍內,婦女的投票權是直到1920年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時才得到確立。
1868年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賦予非洲裔美國人公民資格,1870年的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賦予非洲裔美國男子投票權,但是美洲印第安人直到1924年才獲得公民資格和投票權,而亞洲移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獲得公民資格。亞洲移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的子女因出生在美國而自然成為美國公民,但是他們的父母一直沒有得到歸化的權利。中國移民從1870年起就被法律規定不可獲得公民資格,1943年,國會出於對日戰爭的努力了給予中國移民歸化權。日本移民則是在1952年通過《麥卡倫-沃爾特法》後才被給予歸化權。然而,不管有沒有投票權,美國人從未停止向立法機構提出變革的要求。婦女和非洲裔美國人甚至在還沒有投票權的時候就積極地參與請願、抗議和遊說等公共政治程式。由於立法機構向民主參與敞開,因此公共決策過程是包容性的,儘管當時的許多參與者對其進度感到不滿。
普遍選舉權
造成美國在實行普遍選舉權問題上的猶豫不決的原因之一,要被歸結於18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英國模式,就象那個時代盛行於其他國家的模式一樣,基本上就是一名男性國王以及議會和法官,依據的是混合制政府和土地所有人權利學說,而大多數土地所有人是男性。 但是,大部份討論權利和自由的政治理論和修辭似乎都提出,這些權利和自由具有普遍性。由此,英國人的權利在經過美國人的詮釋後,形成了1776年革命的憲法基礎,從而剔除古老的英國憲法中的暴政成份,保留對美國人有益的內容。如何在實際中做到這一點,則是州憲法會議和聯邦憲法會議的代表所面臨的工作。
在18世紀末期的諸州憲法會議上,代表們草擬的檔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具體體現和擴大美國殖民者的權利。馬里蘭州放鬆了對選舉州憲法會議代表的財產資格要求。喬治亞州建立了一個請願機制,並由此在1789年、1794年和1797年制定出新的憲法。1797年的憲法中包含了一個修憲程式,而不再需要通過憲法會議進行修憲。
麻塞諸塞州1776年開始的一個制憲過程最終提高了人民對修改憲法中的權威。麻塞諸塞州立法機構(當時叫General Court)請求本州各城鎮授權議會在下次開會時起草一個憲法。這一建議的命運掌握在城鎮而不是多數選民手裏。波士頓和另外八個城鎮拒絕授予立法機構為本州起草憲法的權力。在隨後一些年當中,這些城鎮授權立法機構確認憲法。但是最終,這些城鎮的居民通過在沒有通常的財產限制的情況下的投票,拒絕了這一檔。1779年,立法機構做出讓步,允許人民在他們的城鎮選舉憲法會議代表。憲法會議在1780年產生了麻塞諸塞州憲法,這個憲法最終贏得了確認,在其歷史過程中確立了幾個原則。首先,憲法必須由當選代表開會起草。第二,必須保證人民享有通過選舉和修訂程式進行參與的機會。最後,人民必須有投票批准憲法的終極權利。
自由和財產
麻塞諸塞州憲法的制訂過程是1787年各州代表彙聚費城、起草聯邦憲法的背景之一。美國憲法會議的另一重要背景是,自由與財產這兩個因素的關係在立法考慮中的發展變化。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對美國人思考自由與財產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洛克提出,人民同意生活在一種共同體下,以便政府能夠貫徹自然法和權利。人的自然權利包括擁有自由和財產。美國人十分珍視這一思想,因此在他們的政治與憲法修辭中均依照財產法的概念來闡述個人自由:美國人可以擁有自由。洛克也認為生命和自由取決於財產,但是個人對財產絕不能揮霍使用,也不能排斥他人利用自然及其恩澤。因此,1787年憲法會議的代表們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最好地保護擁有私人財產這一自由的果實,同時最好地保護人民從這塊土地上獲取恩惠的權利。
憲法會議的代表在美國《憲法》中創立了一個共和形式的政府,這一政府平衡多種利益,同時包含混合制政府的一些成份。混合制政府的概念融合了君主制、貴族制以及全民政府的歷史成份。這三種政府形式都傾向於存己排異;如果不從憲法上加以制約的話,這三種政府形式中任何一種都會導致極端形式的專制、寡頭政治和民主。這三種對待權力的傾向當中的每一種都有可能威脅人們在私有財產中的自由,然而要維持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每一方的利益都要得到體現。憲法會議的代表找到並實行的解決辦法是, 將權利分散於政府的不同分支中,同時,不同機構之間的功能又有所重疊。重要的是,這種重疊製造了一種平衡機制,每個政府分支具有足夠的權力來平衡其他分支。
國家一級的立法
承襲18世紀的形式,聯邦立法機構由兩院組成:眾議院和參議院。各州各選區的選民通過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眾議員。參議員最早是由州議會選舉的。為了平衡非富有階層的利益和有產階級的利益,聯邦憲法會議的代表當時決定,參議員由州議會選舉產生,以便保證有產階級在美國參議院中得到代表。直到1913年有了美國憲法《第十七條修正案》後,美國參議員才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根據《憲法》,眾議院和參議院構成國會,國會有權制訂和通過法律。美國總統有行使這些法律的權威。雖然《憲法》沒有明確規定,但是總統也可以通過讓他所屬黨派的議員在國會提出議案來啟動某項立法的程式。聯邦司法分支擁有詮釋法律的權威,這一權威很快體現在美國最高法院就法律是否符合《憲法》所做的裁決中。總統可以否決一項法律,但是國會可以使總統的否決無效。對被最高法院裁定不符合《憲法》的法律可以進行修改,使之不再被法庭判為違憲,但是國會如果希望推翻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也可以提出憲法修正案。這樣一個權力重疊的體制,既保存個人權利,也保護私人財產。
州一級的立法
美國州一級立法體制的發展情況是,每個州都建立了和聯邦政府相似的政府結構,但是各州的立法傳統不盡相同。一些州的議會每年開會,將多數時間用於立法。另一些州的議會則來年開會,會期很短。州議會為本州立法的權威與國會為整個聯邦立法的權威類似。一些州憲法規定,修訂州憲法要經過選民直接表決,或者通過提案和全民公決的方式制訂法律。這樣的過程使普通公民能夠提出法律或規章議案,然後在全州通過公民投票進行表決。
立法:權力的分離
無論立法或修憲是由公民投票決定還是由議會討論產生,這些行動都服從於司法審議。在州和聯邦傳統中,法院有權審議立法,決定它是否符合憲法。不過,在制約與平衡的概念中,法院並不完全獨立於政治體制的其他部份。州法院的法官通常是定期選舉產生。聯邦法官是終身任命,但是,州法官和聯邦法官若有不當行為,可以受到州議會或者國會的彈劾。在某些情況下,州長有權任命法官。如今常見的現象是,美國法院對案件的裁決在實際上發揮制訂法律的效力。立法機構制訂法律和司法機構制訂法律的根本不同在於,法院只能裁決當事人提交的案件。立法機構的立法範圍要廣泛得多,但它們也受到憲法以及英國普通法傳統的限制。法院在裁決案件時要考慮憲法的明文規定、以前的判例法、普通法傳統以及公共政策。
總之,美國立法體制的基礎在於權力重疊。州和州憲法存在於由國會、總統和聯邦法院系統主導的聯邦體制內,而聯邦體制又受美國《憲法》的制約。
舉例來說,聯邦《憲法》的商務條款給予美國國會"制定對外以及各州之間貿易規定"的權力。美國最高法院將《憲法》這一條的解釋為,限制州一級制定有礙州際貿易的州與州之間的貿易規定和州內貿易規定。1964年,對《憲法》這一條款的詮釋擴大了國會的許可權範圍,使之包括依據1964年的民權法制定公共住房規定,禁止在出租旅館房間時有歧視行為。
州和聯邦利益的重疊與互動在實際中如何運作取決於許多情況。下面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國會並沒有明確的權力來告訴各州如何規定它們的公路行車速度。這一決定權根據各州憲法和法律條例可以屬於州議會、縣行政委員和市議會。在20世紀,一些州規定機動車輛公路行車時速為每小時65英里,大卡車行車時速為每小時55英里。另一些州認為,將多車道高速公路的行車時速定在每小時75英里更為合理。人口稀疏、城鎮間隔遙遠的州所設定的時速限度則是在具體情況下"合理"即可。在蒙大拿州,駕車人開每小時70英里還是開每小時120英里完全視道路情況和行車條件而定。在那裏開車和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沒有什麼兩樣。但是,當美國在70年代面臨能源危機的時候,國會許多議員認為,要節約能源,就必須把全美國的行車時速限定在每小時55英里。於是國會使用其掌管錢財的權力說服州議員改變州法律。簡單地說,國會告訴各州,如果他們不將自己的時速限制改為每小時55英里,就不會得到成百萬美元的聯邦高速公路撥款。很快,美國全國人人都以時速55英里的速度開車。州議員可以選擇,他們選擇了聯邦撥款。
圍欄法和聯邦制
今天蒙大拿州公路上的牛是另外一個聯邦體制內立法多樣化的例子。牛是否應該不受限制地隨便跑是一個與美國同時誕生的問題。殖民地立法人士必須決定牧主是否應該把他們的牛圈起來,以保護農民的莊稼和園子。修圍欄會增加牧主的開支;允許牛到處亂跑又會損害莊稼,因而使農民受到損失。然而,農民有普通法來對付牧主,如果農民能抓住牛禍害莊稼,就可以扣住它,找到主人後,把他或她訴上審判法庭。
立法人很快決定制訂法律,要求牧主修建圍欄,這些法律中包含了合法圍欄的定義。這一傳統在美國一直持續到19世紀定居點延伸到美國中部大平原時為止,即東經100度以西相對比較乾燥的地區。在多林木的東部各州,牧主修建圍欄,由鎮檢查員決定這些圍欄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而怒不可遏的農民還是會把牧主拖上法庭。但是,有合法圍欄的牧主現在在庭上能為自己辯護。在大平原地區,19世紀的牧場養牛業及其相關行業為了降低成本,力爭讓立法機構實行開放放牧法,並設法改變了圍欄法的要求。根據這些法律,如果莊稼和園子主人希望在莊稼和園子遭受牛的損害時得到賠償,他們就必須支付圍欄用費。隨著養牛業在19世紀80年代的衰落,開放放牧法在後來的幾十年也逐漸削弱。但是包括蒙大拿州在內的一些州在20世紀還是保留了這一法律。
今天,在蒙大拿等州的州際公路上,人們可以看到牛被圈在用納稅人的錢修建的圍欄裏。不過這倒不是基於西部的開放放牧法,而是因為美國駕車人的安全受到威脅。聯邦撥款修建圍欄,以免駕車人和行人受到傷害。在實行開放放牧的州的公路上很少見到圍欄,路上設置了標記,警告駕車人路上可能會有牲畜。圍欄法和公路法清楚地顯示,為維持一個有良好規則的的社會,地方、州和聯邦立法機構在美國體制中有不同的權威,扮演不同的角色。
行政管理機構
美國還有另外一個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功能的立法機構,即19世紀建立的行政管理機構。行政管理機構的先驅是1866年創立的紐約市衛生委員會,但是,是鐵路委員會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把行政管理機構的概念帶到公眾面前,並受到司法審視。行政管理機構通常由一組被任命的專家組成,在沒有立法機構參與的情況下制訂公共政策。
在隨後的幾十年間,司法人士對於這種將立法權威不恰當地下放給行政管理機構的做法一直感到擔憂,但是在20世紀初,行政管理機構獲得了相當大的行政和憲法權威,其制定規章的範圍集中在公共福利領域,涉及從公共衛生、火車票價、到白尾鹿打獵定額等。立法人的想法是,有權威的專家最有資格制訂涉及複雜的經濟和社會系統運作的規則。鐵路、電力、天然氣、或者貨運價格涉及到複雜的經濟計算。為了制訂這些價格,專家們一起共同聽取經營人士和消費者的意見。有關委員會的專員正式聘用專家,分析各方提出的證據。在考慮了所有證據後,委員會從公共利益出發,公佈行業規定。這些規定服從於司法檢查,所謂的行政法也就因此而產生了。
行政法由憲法、法令、機構和普通法組成。行政管理機構是法令、憲法條款或依據法令發出的行政命令的產物。行政法主要是從法官裁決所形成的判例法以及不同行政機構制訂的規章中產生。從歷史上看,在1930年代初以前,法院所關注的是設立行政管理機構所涉及的憲法問題,如:立法機構是否可以把權力下放給行政管理機構。從1930年代起,法院一直在仔細注意行政管理機構制訂規章的程式以及行政管理機構官員的決定權問題。行政機構必須保存制訂規章過程中所收到的證據,並將他們根據這些證據做出決定的過程的記錄存檔。無論一個機構是制訂電話價格還是起草環境規則,司法部門是確定這一決定程式是否合法的仲裁人。如今,美國全國範圍工商活動所必需的許多規定是由州際商務委員會和環境保護局制訂的。
當一個行政管理機構制訂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時,這個機構必須保證民眾有向立法人士表達意見的途徑。根據制訂規章的法律程式的要求,公眾必須得到這一程式開始的通知,必須舉行公開聽證會討論涉及的問題,必須給予公眾就擬議中的規章發表意見的機會,必須將新規章公佈於眾。一個行政管理機構的負責人通常是由州長或者總統任命,由立法機構審查通過。公眾有瞭解這一審批過程的權利,對聯邦政府機構任命人士的審批過程往往有電視轉播,得到媒體報導。公眾利益組織經常在公開聽證會上作證,通過媒體公開他們的立場。這些任命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行政和立法分支的權力重疊也同樣顯然。
民主決策
美國人有遵紀守法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自願遵紀守法的行為來源於一個傳統,即:公民在許多場合有機會參與立法過程。美國的人口和文化雖然非常多樣化,但是,美國的民主選舉政治體制、代表制立法機構以及公眾對立法的參與,都使美國人民與立法息息相關,也使他們對個人權利和財產權的穩定具有信心。對個人權利和財產權的定義和保護方式幾百年來發生了變化,但是今天,無論是在都市公寓樓還是起居室,或是鄉村市政廳,社區裏的人們在繼續制訂法律,他們知道,要維持一個有良好規則的的社會需要每個人親自關注民主決策過程。
美國經驗雖然不一定適用於每個地方,但是有如下幾條基本原則可以保證立法的民主化:被管理者的贊同;在所有立法階段都有人民的參與;向公眾敞開立法過程 ─ 或通過投票、請願、訴訟,或通過司法審查法令、行政規則規章以及行政行動;遵循治理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政府機構間的制約與平衡、共和制政府、民主選舉。根據憲法運作並根植於民有、民治、民享傳統的聯邦和州政府,擁有互相重疊的權力。
相關讀物:
Gordon Morris Bakken, Law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0)
Douglas W. Kmiec, and Stephen B. Presser, Th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nderson Publishing Co., 1998)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John Phillip Rei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4 vol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1987, 1991, 1993)
Melvin I. Urofsky, and Paul Finkelman, A March of Liber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作者介紹:
戈登?莫利斯?巴肯(Gordon Morris Bakken)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的歷史教授。他擁有威斯康星大學的理學學士、理學碩士、哲學博士和法學博士學位,著作有14本書和38篇文章和評論。
9楼
《論民主文集》(6)
獨立司法體制的作用
菲利帕?斯特魯姆 撰文
"美國許多法學家認為,法院對人權領域的問題從憲法上
做出審理,這是我國的一大特徵與驕傲。我贊成這個看法。"
─ 最高法院法官 露絲?巴德?金斯伯格
****************
美國2000年的總統大選曠日持久,遲遲未見分曉,這使許多人為之驚愕不已。決定勝負的選票在佛羅里達州,然而在選舉結束多日以後,人們疑問重重:佛羅里達州的某些選票是否因為技術設施故障而被遺漏,果真如此又該如何處理?佛羅里達州議會介入進來;若干州法官也介入進來。佛羅里達州州務卿和聯邦國會一些議員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講話。候選人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和阿爾?戈爾(Al Gore)的支持者,紛紛在佛羅里達州和美國全國各地示威遊行。
這場爭議案被提交到美國最高法院。法院做出的裁決在實際上宣佈了布希對戈爾的勝利。
至此一切結束。戈爾發表了祝賀布希當選的演說。示威的人群各自打道回府。未能奪得總統寶座的那個党的政治家們在電視上宣佈,現在是齊心協力處理國家事務的時候了。對於法院的裁決,決非人人皆大歡喜,但幾乎人人都認為,必須接受這一裁決。某些人嘖有煩言,認為某幾位法官有政治偏頗,但是沒有人懷疑,法官們是在獨立于其他政治當事人的情形下做出他們的決定的。
聯邦司法體制保持獨立,而且社會上公認這個體制做出的決定必須得到遵守 ─ 這正是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徵。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法院擁有近似美國最高法院的這種在裁決社會爭議、解釋國家憲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非凡權力。在這次選舉爭議之時正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曾在若干年前說過,美國的司法體制是"我國政體中的禦寶之一"。
人們常問到的關於美國司法體制的問題涉及兩個方面。第一,美國讓若干通過任命上任而非民選產生(而且是終身任職)的法官確定哪些是政府其他部門可以採取的合法行動,這是為什麼?第二,這樣一種體制化的權力怎麼能符合民主政體所蘊涵的由多數人決策的原則?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美國人的政府觀念。
聯邦司法體制的創立
起草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89年美國《憲法》(Constitution)的開國先賢深信,人民的權利先於政府而存在。他們在《宣言》中宣告,人的權利與生俱來,政府的宗旨在於維護和增進這些權利。例如,政府必須維護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這是需要有刑事法律和執法官員的原因。
但是,《憲法》起草人提出,如果說,新政府保護人民互不侵權,那麼,又由誰來保護人民不受政府侵權呢?政府可能犯錯,政府可能暴虐,政府可能濫用人民的信任,剝奪人民的權利。美國政治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深信一切體制機構都存在腐敗的可能,所有政治人物都可能受腐蝕,不單是受到有形的金錢的引誘,而且還會受到一種危害性更大的引誘,那就是:以正義的化身自居。掌握權力的人很容易認為,他們自己想做的事理所當然是正確的。這在民主制度下更是如此,因為政治人物可以讓自己相信,既然他們是由人民選出的,這就證明人民信賴他們會做出正確的決定。《憲法》起草人當時已在考慮,用什麼辦法,既可以使政府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保護公民,又不至使政府強大到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堡壘?
他們得出的答案是,通過份割權力來制衡權力。政府要分成三個分支,即總統、立法部門(國會) 與司法部門。國會非經總統同意,不能通過法律;總統非經國會同意,不能推行政策;國會和總統二者都要由司法部門來問責,司法部門按照《憲法》所授予每一分支的許可權來評斷國會和總統的行動。要由司法部門來充當《憲法》的最後解釋者,而《憲法》則是說明主權人民對政府行為的要求和政府權力所受限制的最終檔。如果兩大"政治分支",即總統和國會,企圖跨越這些界線,公民們就可以訴諸司法體制,以《憲法》為依據,向總統和國會的做法提出挑戰。司法體制此時就會予以干預,廢除那些同《憲法》相抵觸的法律。
正如《憲法》的一位起草人曾經所說,司法體制本身既無財力,也無武力。司法部門無法動用軍隊或員警來執行其法令,也無法扣住另外兩個分支的預算。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顯示自己在政治上是如此的獨立,對人民的權利予以如此的保護,以致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感到非服從其法令不可。
司法體制若要能夠無所畏懼、不偏不倚地發表意見,若要能夠真正保持獨立,就必須處於另外兩個分支的控制之外。所以,美國《憲法》規定設立最高法院。《憲法》還責成國會設立若干下級聯邦法院,所有這些法院的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國會的上院)多數票確認。第一屆國會建立了這樣的一個聯邦司法體制,它由若干初審法院和中級上訴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組成,以最高法院為上訴終審法院。所有各級聯邦法官都是終身任職(而且按照法律規定,法官的薪資不得減少)。因此,他們不必擔心會因為做出不合眾意的裁決而被罷職。 一個聯邦法官可以自行選擇離開司法體制另就他職,也可以辭職去參加競選,儘管後一種情形很少出現。在級別較低的聯邦法院供職的法官也許希望得到進入級別較高的聯邦法院就職的任命;但是,同樣地,一個法官在做出裁決時知道,無論裁決會如何激怒政治人士或是一般公眾,他或她的職位仍都是終生穩如泰山的。
上述一段話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聯邦法官們受任是為了確保按照《憲法》所說那樣,使人民的意志高於一切。而另一方面,這種終身任命意味著,他們可以做出被人民認為是錯誤的、同大眾意志背道而馳的裁決。既然法官是由總統和議會的政治家們所挑選的,那麼,法官們做出的裁決難道不會具有黨派傾向,而非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或《憲法》的指意嗎?由此引出下一個問題:挑選法官的程式。
法官挑選程式與司法獨立
所有空缺的聯邦法官職位,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的職位,都由總統提名任職人選;總統當然傾向于選擇一些可能與自己觀念相同的人士。最低兩級聯邦法院的管轄範圍按地理區域劃分;由於參議員在決定是否確認總統提名的人選時往往尊重同事的取向,因此總統在提名某一地區的聯邦法官人選之前,通常先要同代表該地區的參議員協商。不過,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這樣了,因為最高法院管轄全國。20世紀後期的歷任總統還形成了一個習慣做法:在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選時,照顧到地域分佈、宗教、種族和性別,道理是,這樣做可以提高當代法院的信譽。
然而, 法官的終身任職制給總統影響最高法院法官的能力帶來限制。雖然對法官人選的觀點可以通過他們昔日作為政界人物或是作為下級法院法官所做的決策、決定而得以判斷,但是,這並不一定保證這位法官在上任後會如何斷案。例如,1953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命厄爾?沃倫(Earl Warren)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當時他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加利福尼亞州司法部長的沃倫,曾主持將該州的日裔美國人遣送到移居營的行動,而且在擔任該州檢察長和州長時,沃倫採取了對付犯罪活動和犯罪分子的強硬措施。但是,沃倫在擔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後,卻對最高法院一致做出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為違憲的裁決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於沃倫的影響,他所主持的法院在20世紀60年代對《憲法》做出的解釋認為,過去普遍實行的給予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式中的保護沒有達到《憲法》要求。沃倫的最高法院還推翻了一個傳統,在立法選舉中不再讓鄉村地區公民的選票比城區居民的選票具有更大的份量,據說艾森豪威爾對此感到如此之惱火,以致做出表示,早知如此,當初決不會提名沃倫擔任法官。
沃倫做出這些裁決固然在部份程度上有他個性的原因,但是,他這種在施政哲理上似乎改弦更張的做法,也反映了最高法院許多法官的司法生涯中的一個明顯現象。他們當中很多人擔任過民選產生的公職,在這種職位上,滿足選民要求和競選連任的需要使他們專注於地方性政治因素,而這恰恰是《憲法》起草人當年設立終身法官制度時所要設法避免的。其他一些未來的聯邦法官,有些最初在州法院供職,在那裏,並不需要對聯邦《憲法》加以解釋,有些則在下級聯邦法院供職,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憲法》的解讀有誤,最高法院會予以糾正。
但是,這些法官一旦進入最高法院,就再也沒有必要取樂民眾情緒了。他們很快就認識到,自己是國家根本大法的最後仲裁人 ─ 他們如果犯錯誤,再也沒有更高法院可以糾正;於是他們經常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憲法》中那些崇高的字句究竟和應該包含著什麼意思。
任期長久也對司法獨立產生作用。在法官長達數十年的任期內,原來一些會導致總統決定提名或不提名某人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問題可能已經不再具有政治意義,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提名這位法官時本來並不曾料到的議題,倒可能成為重大的政治爭論焦點。這兩種現象都是總統所始料不及的。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1969年任命下級聯邦法院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時,男女平等問題還沒有進入最高法院的議事日程。尼克森無從預見這個問題日後會成為70年代伯格法院的關鍵議題,他也無從按照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來挑選法官。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法官同任何人一樣,都是公民。他們同我們一樣,也必然反映出在自己成長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一些信念。與此同時,我們這個的社會價值觀不斷演變(如同所有社會一樣),科技不斷發展,並隨之產生新的法律問題,而他們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他們同法院外的人交流,他們讀報紙,他們看電視。他們知道有哪些問題對於社會變得如此重要,以致現已躍居國會、總統和州議會議事日程之首。當法官要將1787年制訂的《憲法》中的字句,像"州際貿易"或"適當法律程式",應用于具體案例時,他們必須在同時意識到,"貿易"在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中的含義,或者哪一類"法律程式"被當今社會認為是充份的。
法官們固然有保障不受一時社會風氣及人欲的左右,但他們不會在真空中生活和判案。司法獨立決不意味同人民的意志和多數人的願望一刀兩斷,儘管它確實要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美國制度中還安排了另外兩種對司法權的制衡。聯邦法官雖然通常終身任職,但其實他們是有"良好表現"的基礎的;法官如果犯了刑事罪或是有其他不端行為,將受到國會的審判,結果可能導致被罷免。此外,國會還可以通過立法將某一法律領域劃出最高法院管轄的上訴範圍,比如,國會可以決定,最高法院不得受理任何涉及來自下級法院的涉及宗教或種族歧視的上訴案。
曾有少數下級法院的法官被國會撤職,但還不曾有最高法院法官被罷免,儘管最高法院的許多裁決曾遭到不少國會議員的聲討。國會對自己在上訴權問題上的權力,從不輕易動用。國會如此克制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法院的運作方式。
最高法院與憲法解釋
歷史上,在美國《憲法》起草時,人們的觀念是,聯邦政府將具有十分有限的權力。美國獨立戰爭1776年開始後,組成聯邦的13個前英屬殖民地曾經宣佈各自是擁有一切政府權力的獨立國家。戰爭勝利後,它們認識到,有必要作為一個共同的實體處理對外事務並統一全國的貿易標準;但是,它們仍然相信,為了實現這些職能而設立的全國性政府不在公民生活中占首要位置。在諸如公共安全、教育、福利、保健、本地貿易等方面,各州應該保持對日常事務的控制。
因此,《憲法》以十分籠統的措辭表達了人民的授權。例如《憲法》有一處條文授權國會管理與外國的及"州與州的"貿易。在貿易大都就地進行的18世紀, "州與州"所指的是真正跨過州界的貿易。經過19世紀的工業革命、20世紀的技術革命和21世紀初的這種全球化,這個概念遠非像過去那樣分明了。現在,任何一個州的商店裏的貨物,都幾乎全是在別的州 (或是別的國家 )生產的,美國人民所使用的基本商品都有賴於州際貿易以及國際貿易。公司變得全國化(和國際化)而非僅僅具有地方性。如果某個州要實施保護公共安全與福祉的法規,有關公司可以轉到其他地方,不再在這個州做生意。那麼,由誰來保護消費者免受偽劣商品和有害健康的商品的傷害呢?
從20世紀30年代起,最高法院以對貿易條款的這樣解釋做出回答:聯邦政府可以管理有任何帶有跨州成份的貿易,無論這個成份多麼微乎其微;實施管理的目的更多地出於對公共福祉方面的考慮,而較少與貿易本身有關。其結果是,舉例說,如果一家工廠所使用的原料來自州界以外或是製造的產品將行銷其他州,那麼聯邦政府就可以對廠內的衛生條件予以監督。工廠和商店雇員的工資和工作時間也屬聯邦政府管理的範圍,因為顯然,他們所生產的許多商品將到外州出售。在美國,食品和藥物非經聯邦政府批准,不能上市銷售,顯然也是因為它們跨越了州界。實際上,最高法院對含糊的貿易條款的如此廣義的解釋導致形成一項國策,推動創立了一個有限度的福利國家,使政府擔負起維護公民健康、安全與福祉的重大責任。
《憲法》中的另外一些條文也得到最高法院類似方式的解釋。幾個世紀以來,最高法院在一個遵從美國憲法傳統的釋憲框架內,本著法院對社會需要的理解,對《憲法》的一些早期規定做出解釋,使之適合社會需要。這帶來雙重結果。
其一,由於最高法院以一種演進而又尊重傳統的方式解釋《憲法》,公民不認為有修改《憲法》的必要。今天的《憲法》只包含27個修正案,而且其中10個還是在第一屆國會就做出的。考慮到18世紀末葉的美國同今天的美國有多麼大的差異,修正案的數目可謂寥寥無幾。
其二,由於選民對最高法院解釋的結果感到滿意,最高法院逐漸贏得一種近乎神聖的地位。最高法院就2000年總統大選獲勝者問題公佈意見後,舉國上下都予以接受,這表明,人們認定,最高法院是有能力解釋《憲法》規定的獨一無二的機構。每當總統和國會建立某項法規的時候,人們都有一個當然的假定,即這些熟悉《憲法》規定的機構相信其所通過的法律符合《憲法》。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認為該法律違反了《憲法》所劃定的政府許可權因而予以推翻,那麼,這項法律就將無效作廢。由於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做出裁決時會寫明所做決定的法律根據,因此,國會有時候也可以將被推翻的法規做一番修改,使之符合最高法院的裁決。不過,選民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依靠的最主要手段是修正《憲法》 ─ 但我們已經看到,這並不經常發生,原因是,人民信任最高法院,而這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最高法院在維護個人權利上的作為。
聯邦司法體制與人權
美國《憲法》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憲法所保護的權利種類 ─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在刑事司法體制中獲得公正審理的權利 ─ 意味著,多數派往往是權利的對立面。如果多數人熱衷相信某一主張,那麼這個多數派不會歡迎有相反的主張出現,而且可能傾向於壓制相反的主張。畢竟,群體的福祉是會受到人們所持的觀念的影響的。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同樣熱忱地信奉某一宗教,那麼,似乎在向這種宗教提出置疑的其他宗教就會成為不受歡迎的異己主張了。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政治制度的起點就是個人及其權利。《憲法》給政府的行動劃定了界限,推而廣之,也給多數人對個人的控制劃定了界限。《憲法》將權利包含其中,這實際上是規定出生活中的那些必須讓個人有權按自己的最佳考慮做決定的方面:同意或者不同意多數的主張、從事本人認為合適的信仰活動,等等。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當個人認為是權利、但卻同多數的意志相抵觸時怎麼辦?能不能信任多數派會不顧自己的強烈感情而尊重關於個人權利的原則呢?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憲法》起草人對此的回答是:將維護個人權利的職能交托給多數或是交托給由多數所選出的政府機構將是天真的做法。必須創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無論在多數派的反對情緒多麼激昂的情況下,它都將無所畏懼地伸張人權。
各個聯邦法院十分認真地擔負起了人權 ─ 在美國通常稱為公民自由和民權 ─ 衛士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將這些人權擴大到當年《憲法》起草人所無法預見的範圍。例如,憲法上沒有提到"隱私"這個詞,但是,最高法院從保護不受無理搜查和保護通訊自由的條文中看出保護隱私權的意向。言論自由權,經過最高法院的解釋,不僅適用於電視和互聯網,而且還適用於非語言的交流形式,如藝術表達和富有政治象徵性的穿戴等。
聯邦司法體制在伸張人民的權利時,一方面能夠以非如此獨立的法院所無法做到的方式、不受民眾情緒左右地遵從《憲法》規定,同時又鮮明地確立了自己作為政治生活互動體制一部份的地位。1954年,厄爾?沃倫領導的法院一致裁決,學校中的種族隔離違反了《憲法》給予所有人以平等法律保護的規定,從而間接承認並且鼓勵了新生的民權運動。最終,最高法院感到,它不能將《憲法》解釋為連私下的種族歧視也屬禁止之列,但是,它的裁決促使國會通過了一些禁止私下種族歧視的法律 ─ 當國會制訂的法律在執行過程中遭到反對、被訴諸法院時,最高法院維護了這些法律。當沃倫?伯格領導下的法院第一次裁決男女平等屬於《憲法》問題時,它實際上對婦女地位正在發生的變化予以了承認,並且給方興未艾的婦女運動帶來保證,即這方面的申訴會得到政府起碼一個分支的認真對待。最高法院所表明的就是:那些不合眾意的人,那些另類的人,那些質疑現存方式制度的人,當他們申明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同樣會得到正規審理。
這,歸根結底,就是法官為何由任命產生以及為何終身任職的理由。正如前面提到的總統大選中所出現的情況,公民很可能不同意最高法院做出的某項具體裁決。但是,司法體制的獨立性給了選民一個保證,即最高法院做出的裁決幾乎一向基於法律而不是基於黨派政治,基於貫穿一切的民主原則而不是基於一時的激動情緒。獨立司法體制最終的作用是實踐美國的這樣一個信念:多數人的統治,只不過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個方面。民主制度還包含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即保護個人權利。提供這種保護,是聯邦司法體制的首要職責。
相關讀物:
Henry J. Abraham, The Judiciary: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10th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ncent Blasi, ed., The Burger Cou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ter H. Ir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Viking, 1999)
Anthony Lewis, Gideon's Trumpet (Vintage Books, 1999)
Robert G. McCloskey,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David M. O'Brien, 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5th ed., W.W. Norton, 2000; 4th ed., ppk., W.W. Norton, 1996)
---------------------
作者介紹:
菲利帕?斯特魯姆(Philippa Strum)是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布羅克倫迪安氏贈款專聘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韋恩州立大學吉布斯氏贈款專聘憲法學客座教授。她在美國政府學領域,其中包括美國司法體制和人權方面,有多項著書和文章。
10楼
《論民主文集》(7)
總統的權力
理查德?M?皮烏斯 撰文
"美國總統職權所要求的不僅是從戰場後方發出響亮的宣言。它要求總統將
自己置身於酣戰中;他要滿腔熱情地關懷在他領導下的人民的命運……"
─ 約翰?F?甘迺迪總統
****************
美國總統被稱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行政領導職務,然而,從許多方面來說,它又是最受法律限制的職務之一。總統擁有巨大的法定權力,但是,由於憲法規定的制衡和種種法律限制,在職總統大都體會到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所表述的感覺:"總統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大家做那些本不必經他要求而應該做的事"。總統權力的最大極限往往取決於說服的力量而不是命令的力量。
設立總統職位
《憲法》第二條對政府行政部門的憲法權力做出規定,即設總統一人,通過(選舉團方式)選舉產生,任期固定為四年。
任何讀到《憲法》第二條的人都會立即驚訝地發現,它對總統選舉的機制規定得十分詳盡,而對總統就職後的權力卻只有寥寥數語。儘管總統被授予"合眾國的行政權"("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但在總統如何向各部門主管人員下達指示、如何掌控各政府部門或是如何罷免官員等方面,《憲法》無一任何具體規定。雖然總統可以經徵詢參議院的意見和參議院的同意締結條約,但是《憲法》對誰有權力廢除條約沒有規定。總統被稱為總司令,但是對於總統指揮軍隊的權力,或是對於總統同戎裝軍官之間的關係都沒有進一步規定。總統可以召集國會舉行特別會議,有義務向國會報告國情並建議國會採取措施,而且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但是沒有任何條文規定總統有權頒佈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
但是,這些並非不是無意的疏漏。《憲法》起草人是一些諳熟殖民地和州行政管理的務實務之士,其中很多人具有豐富的軍事和外交經驗。他們草擬的關於總統許可權的條款簡短含糊,目的是要讓這部《憲法》能夠在那些對行政權疑慮重重的州議會得到通過。他們並沒有對行政權作充份的界定,也沒有周密地對其加以限制,而是將許多問題留給後代去解決。
因此,憲法語言可以得到兩種解釋。行政權既可以被限制、束縛、制衡,也可以被用作建立由中央政府指導的強大經濟的工具和抵禦外國干涉這個新興國家事務的危險的保障。
提名與選舉
總統提名與選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同總統權力的模糊性有關。最初,《憲法》起草人設想,由每隔四年為挑選總統而組建一次的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提名"五位候選人,然後由眾議院做出最後選擇;選舉團由各州代表組成,大州占強勢。然而,到了19世紀初,政黨有能力為自己的候選人取得選舉團多數,從而形成了延至今天的以政黨主導的制度。到了19世紀30年代,各州的立法議會陸續把選擇選舉人的權力讓給了本州人民,給選舉總統奠定了全民選舉的基礎。
現行的兩大政黨黨內提名制的做法是,首先在州內進行角逐(稱為初選或政黨基層選會),挑選出參加黨全國大會的代表,再由全國大會挑選出本党提名的候選人。成功的候選人要顯示其在籌措經費、刊登廣播電視競選廣告、塑造自己的媒體形像以打動選民人心等多方面的才能。由於必須籌措經費並且組織好媒體宣傳,因而人選的範圍縮小到只剩下一小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大多數不是州長就是參議員,或是副總統。
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儘管小阿爾?戈爾(Al Gore Jr.)獲得的選民票數比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多出50萬張以上,但布希按選舉團票數還是擊敗了戈爾,因此,圍繞究竟選舉團制度是否仍符合時代需要產生了大量辯論。總統大選競選實際上是一場在50個州中爭奪多數的角逐,目標是奪得每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的選舉團票。這個制度的優點是,這些分開進行的"贏者囊括一切"的角逐,突出了國家的聯邦性質,迫使候選人從地域角度而不是單純從選民人口結構來考慮問題。另一個好處是,萬一雙方得票十分接近,重新點票就只需在票數十分接近的州進行,不必要重新提出在全國範圍點票的問題。例如,在2000年,舉足輕重的點票爭議,僅僅出現在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出現在全國所有各地的選區。選舉團制度的缺點是,由於歷史原因,一些小州得到相對過多的選舉團票數,因而其選民選票的份量高於大州。但是,由於大州的選舉團票都將一攬子歸與這個或那個候選人,這促使候選人幾乎會全力以赴地去爭取最大的12個州,而不很在乎其餘的州,尤其是那些他們反正已經遙遙領先或是遠遠落後的州。
採用選舉團制度的最後一個困難是,有可能哪一個候選人都得不到大多數選舉團票,此時,競爭轉入眾議院(各州在眾議院中通過其議員作為一個單位而投票)。這種情況,1800年和1824年發生過,在1876年也幾乎出現。另外,也可能出現候選人雖然贏得選民的多數票但卻在選舉團選舉中敗北的情況,除2000年以外,1876年、1888年也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部份分權
《憲法》起草人認為,聯邦政府的幾大分支之間的分權只能是"部份"的而非"完全"的分權。他們參考了法國人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和英國人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理論,分別設立了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並分別創立了三個分支來行使這三權。但是,為了保持這三個分支之間的平衡,他們決定允許三者的職能有所重疊。
每個分支不但行使自己的本職職權,而且也兼管另外兩個分支的一些職權。例如:總統有赦免權(這是一項司法職權),可以向立法機構提議採取措施(這是一項立法職權)。參議院有責任參與人事任命(這是一項行政職權),國會有通過彈劾審判撤銷職務之權(這是一項司法職權)。法院可以做出普遍適用的裁決(這是一項立法職權),也可以發佈命令(通過職務執行令狀)要求行政官員採取特定的行動。
部份分權的影響表現在聯邦政府的諸多方面。總統對於其他兩個部門的工作有更多的參與機會,但同時,一些按理也許屬於行政部門的事宜(如戰備、外交、內政決策、預算),卻要會同立法部門共同處理。其結果,與其說《憲法》是將各項權力劃分得一清二楚的政府藍圖,不如說是(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愛德華?科溫〔Edward Corwin〕的話)爭奪對美國決策的指揮權的"邀賽書"。
制衡
由此可見,總統是在一個"制衡"體制下行使職權,這個體制的目的就是讓聯邦政府的每一部門都能對其他部門的權力有所制約。總統可以基於憲法的或政策的理由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而他的否決必須有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才可以被推翻。這不但使總統能對國會進行制約,而且也使他能事先將立法部門關注的重點同他自己議事日程上的輕重緩急加以"平衡"(特別是當國會處於對立政黨的控制下),因為他可以事先揚言將否決立法部門正在考慮的某一法案。這樣,國會就可能不得不在通過法案之前考慮總統的態度,以免總統屆時行使否決權。總統對各個聯邦法院的制約是通過他對新的聯邦法官與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來實現的:這一權力具有一種日積月累的影響力,即隨著總統所任命的法官越來越多,將形成聯邦法官中很大一部份人對憲法和成文法的解釋與總統的觀點相近。
但是,制衡對總統的特有職權也同樣有限制作用。例如:總統頒佈的行政命令必須符合成文法,否則聯邦法院就不予以執行。總統任命的高級官員必須經參議院多數票同意。總統行使權力締結條約亦應徵詢參議院的意見和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總統的任何行政命令或(與外國締結的)行政協定,都要受司法部門的審視,聯邦法院有權力以違憲為理由,宣佈該命令無效作廢。
彈劾與免職
對總統的最重要的制約,是《憲法》專門規定,對"重罪和嚴重的行為不端"實行彈劾及免職。上面這個術語來自英國的慣例,其根據是布萊克斯通爵士(Lord Blackstone)的《英國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據布萊克斯通的定義, "重罪"("high crime")指的是對國家的犯罪,如叛國,而"嚴重的行為不端"(high misdemeanor")指的則是重大的腐敗與瀆職行為。美國的憲法體制中沒有規定總統在失去國會信任時去職(而在議會制下一旦失去信任投票意味著辭職)。
總統在經眾議院多數票表決後被彈劾(相當於被起訴) ,隨後在參議院接受審判,審判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懲罰只限於免職,不過,總統在彈劾案中無論被定罪與否,都可受到法院的起訴與審判。
《憲法》起草人認為,設置一個困難的彈劾程式將導致它較少地被啟用;他們的想法完全正確。美國歷史上總共只有三位總統曾面臨彈劾:1868年,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因違反《職務任期法》而受到彈劾(該法旨在防止總統在參議院就繼任人選達成共識前罷免內閣部長),但在表決時以一票之差被宣判無罪;1974年,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針對他隱瞞同水門竊聽案有關的罪行而做出彈劾建議後辭職;1999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被以在民事訴訟案中作偽證和妨礙司法調查之由受到眾議院彈劾,後被參議院宣佈無罪。
總統特有職權
儘管《憲法》的規定以及同相應兩大分支共事的種種困難似乎限制了總統的權力,但是總統有辦法繞開這些困難。有時候他們以自己對《憲法》的解讀為依據,施展很大的總統特有職權(prerogative power)。憑藉著這些權力,他們單方面採取行動,解決一些嚴重的政治爭端或處理危機,事後才向國會和美國人民說明理由,既顯示了他們行使權力的合法性,也顯示了他們的決策的權威性。
開國至今,總統特有職權解決了一些重大分歧。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18世紀90年代初單方面宣佈對英法之戰保持中立,儘管《憲法》中完全沒有授權他這樣做的明文規定。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803年從法國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地區(LouisianaTerritory),雖然《憲法》中並無明文規定聯邦政府有權收購領土。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堅持行使了將內閣成員免職之權,樹立了總統在行政部門中的無上權威,儘管《憲法》對免職權毫無規定。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行使的權力如此之大,以至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克林頓?羅西特(Clinton Rossiter)日後稱那一任政府為"憲政獨裁" ─ 憲政,是指即使在南北內戰時期,仍然照樣舉行了中期選舉和總統大選;獨裁,是指林肯在那個國家危機時期,有時候越出了法律和成文《憲法》所規定的界限。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也依靠過總統特有職權。他同英國訂立了一份行政協議,以超齡驅逐艦交換海軍基地,大大幫助了那些載運軍用物資穿越北大西洋的英國船隊。行政協定不同於條約,不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而這正是羅斯福運用自己的特別權力採取這種國際協議形式的原因。
如果一位總統使用特有職權獲得成功,會產生"正彈"效應,這表現在,他的黨和美國人民會團結在他的身後;反對黨往往會分裂,失去信心;他自行採取的做法往往通過隨後的立法或司法行動得到肯定和合法化。反之,如果總統的行動 ─ 例如杜魯門總統在韓戰期間接管鋼鐵廠以及尼克森總統扣押某些國內項目資金 ─ 受到法院審議,則可能產生"反彈"效應,也就是說,國會很可能會通過一些使得總統更難於動用特有職權的法律。例如,尼克森的做法被法院駁回後,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規定總統如要推遲或取消國會已經通過的撥款,必須取得國會的同意。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和尼克森總統進行的越南戰爭,引起了針對總統作戰權的反彈效應,國會在1973年通過的《征戰權力法案》(War Powers Act)中讓國會得到權力,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要求總統從戰爭中撤軍。但是,聯邦法院曾拒絕以法令要求總統從戰爭中撤軍,儘管有國會議員提出過針對雷根、布希、克林頓三位總統的訴訟案。法院的裁決是,除非國會作為一個整體提出起訴,否則法院不受理個別國會議員的訴訟。
國內政策領導
總統上任時,往往並不具有大刀闊斧改變現狀的權威,除非是在經濟困難時期或是軍事危機中。總統也沒有多少"提攜扶掖 "能力(指投總統票的人也把選票投給一些與總統同黨的競選國會議員的候選人),而且大多數總統本党的國會議員當選時,很可能在自己選區取得了比總統更扎實的優勢(通常得到更多的選票)。此外,總統左右不了國會中的權力結構:他決定不了參眾兩院的黨派領袖、常設委員會成員以及各委員會的主席。而且,制定本黨綱領的議會中的黨核心小組也不由總統主持。
總統執政以4年為一週期。由於要顧及自己連任的前途,因此如果有要求人們作出犧牲的舉措,他們很可能在上任初期提出,這樣,等到接近爭取連任的那兩年,他們就可以拿出"好東西"來同選民見面。所以,如果需要採取緊縮措施,總統會在上任初期提出。反之,國會議員是以2年和6年為選舉週期,即總統上任兩年後,眾議院的全體議員和參議院的三分之一議員面臨改選。因此,總統號召緊縮和犧牲,有可能在中期選舉中使本党議員處於險境。
總統所屬的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幾乎總是要丟失議席。通常,總統的政黨在總統執政的第二年會丟失多達20個議席,到執政的第六年更會多達40個。總統基本無力改變這種趨勢。即使他的政績良好,也很少會在中期選舉中對他本党議員產生效用;但是如果政績不佳,則會使投其政黨票的選民倒戈,支持反對黨。因此,總統本党那些處境較危的議員,可能把總統看作是影響他們競選連任的障礙。
總統在就任的第一年(即"蜜月"時期)往往能如願以償地取得成果,但不無矛盾的是,這一年是他們對自己所應做的事情最缺乏經驗、最少瞭解的時期。隨著經驗逐漸積累,他們對如何能達到目標有了更好的設想,但偏偏這個時候國會中能投票贊成他們的方案的支持者比過去減少。隨著在職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國會的成功率越來越低。在接近任滿時,尤其是如果國會是控制在反對黨手中的話,總統可能會發現,他的預算提案以及對高級官員和聯邦司法法官的提名,在抵達國會山時已是"死胎腹中" 。
聯邦制
美國的國體是聯邦制而非大一統制。這就是說,州長和州議會代表著本州公民的主權,從而形成州與國家的雙重主權制。按照《憲法》第六條,國家主權權力至上,因為國家的《憲法》、法律和條約高於州的憲法和法律。而且,州的官員和國家官員一樣,在宣誓就職時,必須保證維護國家的憲法與法律,即使是需要以本州的憲法與法律為代價。
但是,州政府並不受總統或國家政府部門的控制。固然總統所支援的某些專案可以完全由聯邦官員來執行貫徹,但白宮所贊成的大多數國內專案都需要州、縣和地方官員的協力合作才能成功。鑒於地方上的側重點往往與總統的不一樣,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國家專案會有"聯邦化"與"地方化"之分, 以反映基層的需要。
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領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出現的一些趨勢,加強了總統指導對外事務的權力,削弱了國會對總統的政策施加影響或干涉的能力。佛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繼任者們控制了在對付冷戰對手中至關重要的情報工作,並經常說服國會議員,在國家安全事務中,應該放手讓他們相機行事。總統們施展了他們認為是憲法賦予總統的特有職權,同時運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國會授予他們的龐大權力。
總統在對外事務中大權在握的局面,在林登?詹森和理查德?尼克森時期達到頂峰,有些觀察家把這兩任總統當政的時期稱作"帝王總統政期"("the imperial presidencies"),意指他們為了越南戰爭而擴大使用總統特權。在戰事最初升級時,許多國會議員和美國人民對美國的目的何在一無所知;後來在老撾和柬埔寨的戰事升級也同總統特權有關。國會最終在1973年夏季停止了對印度支那戰事的撥款(當時柬埔寨仍然屬於轟炸目標),不過,國會是在巴黎和平協定結束了美國在越南的作戰行動之後, 才採取行動的。
其後,帝王總統政期引起的反彈導致一些新法律的誕生,這些法律使得國會對在不需正式宣戰的敵對行動中部署美國武裝力量具有發言權(1973年的《征戰權力法案》),並要求將涉及隱蔽行動的特別情報活動通告國會(1980年的《情報監督法案》Intelligence Oversight Act)。另外還有一些法律規定,同外國訂立的行政協定不得向國會保密,凡是美國做出的國家承諾均需國會與總統正式宣佈。在80年代,民主黨占主導的國會給共和黨的總統對中美洲實施軍事干預增加了難度;在90年代,共和黨占主導的國會通過扣壓對一些多邊機構以及聯合國的會費,讓民主黨的總統受到掣肘。
越南後的時期,有時候被稱為總統權力的"後現代"時期,其標誌是,外交事務不分黨派的局面結束,國會對行政部門的方案言聽計從的時代不復存在。如今,無論在外交或是內政事務上,總統都必須取得國會的支持,至少必須得到國會的默許,否則他的舉措從長遠來說就行不通。正如在國內事務上一樣,這意味著總統的說服權力,而不是特有權力,對於他的政策的成敗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
基本原則
美國在總統權力上的經驗或許對於別的國家有可借鑒之處。總統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說服之權",即說服國會和美國人民去支持公共政策中的重大變革,這個制度的運作形態近似於議會制。但是,總統職務又意味著具有特殊的權力手段,也就是,總統在黨派和公眾支援有限的情況下,得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利用自身的憲法權力來解決某項全國性危機。1832年傑克遜的做法便是一例,當時他防止了南卡羅來納州違反聯邦關稅法;1861年林肯也曾這樣做,當時他針對要求脫離的州實施聯邦法,從而加速了內戰的爆發;1940年和1941年,佛蘭克林?羅斯福同英國和蘇聯結盟對抗軸心國的做法,則又是一例。
這些經驗顯示出美國憲法語言上的含糊性的作用 ─ 它使對龐大的權力施加非明確的限制成為可能,從而得以在處理緊急事態時,不給行政部門造成羈絆,不會妨礙果斷的行動。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權的根本問題仍然是:人民怎樣才能不讓擁有龐大特別權力的行政首腦變成獨裁?社會怎樣才能糾正行政濫權行為?美國的理念是,依據下列原則來維護一個有限的、憲政的、民主的政體:部份分權,以使其他分支參與日常決策;實行制衡,以使任何權力都不可能在其合法性不經立法與司法部門審視的情況下長久存在;採取聯邦制,從而一旦國家體制發生問題,州可以發揮作用;實行民主制度,使得總統和他的政黨每隔一定時期就必須接受選民的問責。一個正宗的議會制度可以通過不信任投票或宣佈舉行新的選舉來突破僵局和政策癱瘓狀態。在基於總統任期固定和選舉日期固定的美國制度下,出現僵局的危險隨時存在,但可以通過成功地行使總統最高權力,或者依靠總統的領導作用形成國會和公眾輿論的共識,來減少這種危險。
綜上所述最根本的一點是,總統職權根植於這樣一種政治文化中:既遵從總統的職權,同時又對總統掌握的行政權保持高度戒心。在分權制度下,總統並不體現國家的主權。總統並不是專制君主,不淩駕於法律之上:法院已經裁定,總統在位時也不能免於私人法律訴訟,凡是法官要求在位總統向法院提供證據,總統必須照辦,並且可以受到司法審訊。雖然我們有一些規章允許特工處(Secret Service)調查和逮捕直接向總統發出威脅的人,但我們的法律沒有把對總統職務或擔任總統職務的人表示不尊敬定為犯罪,法律也沒有禁止新聞界或反對黨直接批評總統及其政府成員。這種既對總統職權高度尊重,同時又對行使總統職權抱有適當戒心的美國政治環境,也許是將總統職權保持在憲政範圍之內的最重要因素。
相關讀物:
Richard J. Ellis, ed., Found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rles O. Jones, The Presidency in a Separated Syste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Richard E.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 (Free Press, 1991)
Richard M. Pious, The Presidency (Allyn and Bacon, 1996)
Robert Y. Shapiro, et. al., eds., Presidential Pow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J. Spitzer, President and Congress (McGraw-Hill, 1993)
---------------------
作者介紹:
理查德?M?皮烏斯(Richard M. Pious) 巴納德學院阿多爾福?奧克斯與埃菲?奧克斯贈款專聘美國研究專業教授兼政治學系主任;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文理研究生院教授。
16楼
《論民主文集》(8)
自由媒體的作用
約翰? W?詹森 撰文
"人們一旦看到歲月給昔日分庭抗禮的種種信仰帶來的起落沉浮便會相信……達到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徑是通過思想的自由交流 ─ 對真理的最好檢驗,莫過於它在市場競爭中為人們所接受的程度。……無論如何,這是我們《憲法》的理念。這是一個實驗,而整個生活就是一個實驗。"
─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於1919年
****************
一個社會要被視為真正的民主社會,就應該對公開發表的思想言論有高度保護,無論其媒體是報紙、雜誌、書籍、手冊、電影、電視, 或是最新近的網際網路。 美國200多年來的經歷是一個在一個國家內如何確立言論表達基本規則的有益的實例。當然,這些經歷帶有與美國文化和歷史息息相關的獨特性,但是它們所展示的基本原則對其他民主社會廣泛適用。
作為美國政府制度基石的美國《憲法》,如果不附加旨在維護個人自由的的十條修正案,即《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不會在1791年獲得美國最早13個州的批准的。而修正案中的第一條便確定了媒體的言論自由權,這決非偶然。憲法《第一條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有一段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在起草《憲法》與《權利法案》的開國先賢們看來,文字讀物 ─ 通常是報紙和小冊子 ─ 屬於公開發表思想言論的媒體。因此,《第一條修正案》中使用了"新聞出版"這個概念。貫穿美國歷史,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如同它們在《第一條修正案》中的孿生關係一樣,在公眾和在裁決公開言論案的法官心目中,始終相互關聯。
自由媒體在美國的作用是複雜和不斷演變的,瞭解其歷史發展的最好辦法, 也許是通過觀察美國法院做出的裁決。雖然《第一條修正案》給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保證,但是,是美國的司法系統界定出這一概念在實際中的確切涵義。通常是法院將這個源於18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做出延伸,保護這一權利不受美國社會上對新聞出版自由過多感到不舒服的勢力的損害。
曾格案與煽動性誹謗罪
一般認為,在早年的北美洲大陸的各英屬殖民地,人們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與今天不同。1734年紐約報紙出版商約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的案子便是一個說明。紐約的殖民地政府因曾格印發了一篇猛烈抨擊該殖民地總督的文章,指控他犯有煽動性誹謗罪。《布萊克法律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對誹謗罪的定義是:書面形式的傳播"使某人有可能遭受公眾仇視、羞辱……鄙視、恥笑、……或失尊……。"曾格那篇文章的內容之一是,宣稱總督未經立法議會同意而設立法院,而且擅自剝奪殖民地成員經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曾格通過他的律師對刊印這些指責承認不諱。他只是堅稱自己有權發表對一個公職官員的批評,而只要批評屬實,即使使該官員受到恥笑也未嘗不可。陪審團做出有歷史意義的判決,宣告曾格無罪,進而確立起一項原則,即事實是反駁誹謗指控的依據。但是,陪審團對該案的判決並沒有改動英國的法律原則,也就是18 世紀末葉傑出的法學作者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所有力闡明的凡發表"惡意中傷……言論" 即為可罰之罪。
1798年,由於擔心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潮流可能蔓延到大西洋此岸,美國國會以多數通過一項《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將"書寫、印刷、口頭表述或發表……任何虛假的、誹謗性的和惡意的文字作品"攻擊政府定為犯罪行為。若干個人和報館被根據這一法律受到起訴,其中有出版商詹姆斯?湯姆森?卡倫德(James Thomson Callender)。卡倫德因為曾於1800年將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總統稱為一個"頭髮斑白的煽動者……雙手沾滿鮮血"而被指控犯有誹謗罪。卡倫德本人名聲不佳,即使在當年有時政治粗話氾濫的日子裏,他也被視為一個口出穢言的人物,於是他被判了罪,坐牢數年。在弗吉尼亞州的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801年就任總統後不久,將他赦免。
誹謗案在19世紀
進入19世紀以後,誹謗逐漸由刑事訴訟由轉變為民事性質。也就是說,原來只是政府起訴用文字批評當政者的人,而今一些有地位的個人為維護自己的名譽而開始自行向法院提出訴訟。
因此,直到20世紀以前,涉及在聯邦政府面前維護個人權利的司法案例為數很少。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歷次最重大的憲法案件所涉及的不是言論自由問題,而是各州與聯邦政府彼此的權力劃分以及因政府企圖對企業施加管制所引起的法律紛爭。在當時,美國源遠流長的地方主義傳統,使聯邦政府同個人之間直接發生碰撞的可能性被減至最低程度。
1833年,在美國司法體制中至高無上的最高法院裁定,《權利法案》僅確立聯邦政府不得侵犯個人權利,而州政府不屬受限制之列。這使得在進入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後,各州得以繼續對報紙和其他印刷媒體實行檢查。因此,儘管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以堂皇的措辭許諾了新聞出版自由,但是在美國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各地法院給那些敢於批評政府的人士提供的保護並不一致。從1833年的裁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時期內,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涉及言論自由的案件寥寥無幾。但是,政治自由的文化傳統,加上大量發行的報刊雜誌數量增加,促使作家和報刊漫畫家在這個時期裏始終要盡力拓寬言論自由的限度。甚至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成了漫畫家無情揶揄的對象。世紀交接時期的人民黨政治家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則是另一個對象。
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點是,20世紀初,一些以"揚醜揭秘"為業的記者和作家,以全國發行的雜誌為陣地,揭露商界和政界的腐敗醜聞,這些揭露材料,所向披靡,人相爭閱,在政治上和法規上都引起了重大的變化,對進步運動作為20世紀一支強大的政治勁旅的崛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且為幾十年後從法律上擴大新聞出版自由創造了條件。
戰爭時期的新聞出版自由
1917年,大約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國會通過了"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對未經授權擅自取得、接受和傳播國防資訊加以懲罰。次年,對這一法律添加了一套修正案,通稱"1918年反叛亂法"(Sedition Act of 1918),規定對可能有利於美國敵人的資訊言論施加懲罰。依循這一法律提出的一些公訴案導致美國最高法院就《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條款做出數項裁決。在這些公訴案中最為重要的一宗,是1919年對雅各布?阿布拉姆斯(Jacob Abrams)的起訴案。阿布拉姆斯因為撰寫並散發兩份傳單,批評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美國政府向俄國沙皇提供鎮壓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軍事支持而被控觸犯"反叛亂法"。分別用英文和意第緒文寫成的這兩份傳單只散發在紐約市的小部份地區,而且,阿布拉姆斯提出的批評同美國的對德作戰行動關係不大。但是,美國最高法院還是維持了對阿布拉姆斯的有罪原判。法院的大多數法官的理由是,阿布拉姆斯的行為對社會安寧形成了"明顯而現實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因此可以受到政府的懲罰。
"明顯而現實的危險"這個標準是由最高法院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一年前的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言論自由的另一項裁決中首先提出的。但是在阿布拉姆斯一案中,霍爾姆斯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誤用了他提出的這個評估這類自由言論合法性的標準,他堅持認為,"一個無名人物偷偷散發一種荒唐的傳單" 對社會沒有構成什麼危險。近80年來,在法院對批評政府的口頭、書面和象徵性表達方式是否符合憲法的案件進行審議時,"明顯而現實的危險"這一說法被無數次引用。一些法學家認為,這個標準的可塑性變得如此之大,以至可以說它適用于從完全的新聞出版檢查到完全的言論開放的任何一種公共政策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言論自由的案件顯示出《第一條修正案》中有關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二者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美國最高法院從未對"言論"與"新聞出版"加以明確區分,因為它們常常並存於同一個案子中。例如:阿布拉姆斯聲稱自己有權以文字傳單為媒介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申辯是,他的言論受到《第一條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條款的雙雙保護。一般的規則是,法院並不給予在報紙或是其他媒體上發表言論的人比口頭表達思想的公眾更多的保護。
最高法院的兩項裁決促進了新聞出版自由
將《第一條修正案》作為一條保護個人言論的憲法原則的做法,在1925年涉及一個名叫本傑明?基特洛(Benjamin Gitlow)的共產黨人的案子中有了重大發展。基特洛出版發行了一份小冊子,宣傳採用罷工與集體訴訟的手段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紐約州指控基特洛觸犯了視鼓吹推翻政府為犯罪的州法。美國最高法院儘管維持了對基特洛的有罪判決,但仍然裁定,《第一條修正案》對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的保護,屬於任何州或聯邦政府都不能加以限制的幾項關鍵性的個人自由。法院還援引了1868年批准的《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一段話:"任何州不得……剝奪合眾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任何州,如未經適當法律程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拒絕給予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護。"最高法院的推論是,這項修正案起草人的用意是使各州今後必須同聯邦政府一樣,尊重各項重要的個人自由,而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正是其中兩項重要的自由。
由此,《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詞語開始被作為一種法律杠杆,在個人與州的權力相對立時,它使《權利法案》的保護力傾向於個人。最高法院就基特洛案做出的裁決,實際上推翻了法院在1833年做出的州不受《權利法案》約束的裁決,從而開始了一個持續了40多年的趨勢,使人們根據美國《憲法》頭十條修正案所提出的某些保護做出個人不受州與聯邦侵犯的規定。這個趨勢鼓勵了地方上的言論自由。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個時期內,在有關新聞出版自由的案件中,1931年的一個案子或許具有最重要的意義。這個案子涉及的是,州是否有權限制一份聲名狼籍的揚醜小報《星期六新聞》(Saturday Press)的出版。報紙的出版人J?M?尼爾(J. M. Near)是20年代最惡劣的排外主義與種族主義的鼓吹者。明尼蘇達州議會曾於1925年通過"消除擾亂公共安寧法"。這一法律規定,凡是法官認為某出版物"猥褻、淫蕩、色情" 或"惡意、揚醜與譭謗",即可下令關閉。在這項法生效後不久,一位州法官關閉了《星期六新聞》。上訴時,美國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從憲法角度對一個基於英國普通法和被美國開國先賢所接受的長期立場給予維護,這就是,對新聞出版不應施加"預先限制"。最高法院裁定,雖然偶爾當某人出版了極其惟利是圖的、惡意中傷的或是憑空誹謗的刊物時或許可以實行懲罰,但是,只有在如國家安全等極端情況下,才可預先制止報館發表有爭議的文章。出資幫助《星期六新聞》上訴的芝加哥出版商羅伯特?R ? 麥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說,首席法官查理斯?伊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代表大多數法官就本案提出的論斷,"將作為思想自由的一大勝利而載入史冊。"
"公眾人物"與誹謗法
美國新聞出版自由在20世紀日益擴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最高法院通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中的幾件很有意義的案子所形成的"公眾人物別論" ("public figure doctrine")。這一別論所基於的原則是,一個普通人 ─ 不知名的或是其名字並非家喻戶曉的人,在不受媒體指摘這點上得到的保護,比公眾人物得到的保護要多。而一名公眾人物則必須承受媒體哪怕是不屬實的窘人的批評或指摘,除非他/她能證明發表那一言論是出於惡意。在這裏,對"惡意"的定義是,作者、編輯或播放人發表當時已知不屬實的資訊。如果作者、編輯或播放人不顧忌所發言辭是否屬實,那麼也可以構成惡意。根據"公眾人物別論"提出的訴訟案,其焦點大多數都轉為,聲稱自己受到誹謗或誣衊的個人是否確實被法院定為公眾人物。某人一旦被確定為公眾人物,要證明他/她受到誹謗是極其困難的。
有一個廣告案也許最充份地體現出"公眾人物別論"。在這個案子中,一批希望對民權運動領袖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事業提供幫助的人出資刊登了一則廣告。廣告中提到,馬丁?路德?金在南方各地,包括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曾受到地方執法官員的騷擾。蒙哥馬利市公安局長L ?B?沙利文(L. B. Sullivan)就此起訴《紐約時報》,指責它破壞名譽,理由是該廣告中有某些言過其實的說法以及事實性的出入,有可能導致公眾對他的非議。最高法院的裁決是,《紐約時報》的廣告中有無意的而非惡意的錯誤,沙利文作為一位元公眾人物,不能從《紐約時報》索取賠償。二十多年之後,又有一樁涉及著名保守派牧師傑裏?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的誹謗案被提交最高法院審理。起案原因是,福爾韋爾被當作一份性暴露雜誌刊登的"滑稽嘲弄廣告"的對象。廣告中有關法爾威爾的"事實"全屬憑空捏造。法爾威爾申訴說,他的名譽受因此到了很大損害。但是,最高法院判決該雜誌勝訴,根據是,新聞出版自由給予漫畫家和畫公眾人物諷刺像的人很大的自由度。
保護的層次
美國法院在歷年來就多項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案做出的裁決中,對政治言論比對其他言論給予了更大保護。這並不奇怪,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誕生於對18世紀末葉英國在北美洲的統治的政治批判。上述討論過的那些案件大都涉及政治言論,這並非偶然。但是, 如果說政治言論受到優先保護的話,那麼,哪些類型的言論居於受保護的較低層次呢?
法院認為商業言論屬於較低層次。最高法院一貫裁決,廣告唯有真實才能受到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保護。所以,言過其實以及事實上小有出入的情況在政治言論中可以得到寬容,但是如果出現在電視廣告中,例如在推銷漱口劑或多功能車的廣告中,就得不到司法保護。這樣做的部份原因是,商業言論比政治言論較易於核實。此外,美國法院通常認為,希望通過推銷產品與服務而獲得利潤的強烈動機比政府管制所能產生的"可怕效果"更為事關重要。
在受司法保護的層次中居更低位置的是猥褻資訊。1957年,在"羅斯訴合眾國案"(Roth v. U.S.)中,最高法院認為猥褻與色情材料"根本沒有可取的社會價值" ,因而屬不受保護之列。在很大程度上,與猥褻有關的問題是如何給其下定義。在一個人看來是猥褻的東西,在另一個人看來卻可能是藝術傑作。對某些人來說,詹姆斯?喬伊絲(James Joyce)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猥褻得令人生厭;但是,在最近對文藝界知識份子的一次民意調查中,它卻被奉為20世紀最偉大的英文文學作品。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在60年代中期審理一件案子時說過的一段話,可以代表大多數美國人的看法,即他可能無法對猥褻下定義,但是"當我看見時,我知道。"
可惜,斯圖爾特法官的這句妙語,並不能為評價藝術作品提供有效的法律標準。最高法院通過極其艱苦的努力,在1973年制定出一個判斷猥褻的三段審議標準。它規定,表達方式如有下列情況便屬於《憲法》保護範圍之外:(1) 普通人按照當地社群的標準,認為作品從整體來說是在滿足淫欲;(2) 作品以"明顯令人厭惡的方式"展現和描繪性行為;(3) 作品缺乏文學上、藝術上、政治上和科學上的真正價值。鑒於這套標準相當含糊不清,所以毫不奇怪,最高法院就媒體中的猥褻問題做出的裁決,近30年來始終缺乏明確的方向。從很多意義來說,最高法院的猶疑不定是整個美國社會狀態的反映,即它一邊是力主言論完全自由的力量,另一邊是社會保守主義的力量。
採集新聞與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新聞在發表或廣播之前的採集過程,偶而也受到美國法庭的審理。最高法院1972年曾裁決,記者可被要求向大陪審團說出秘密的消息來源。但是,最高法院於1991年又裁決,新聞出版自由並不禁止州起訴那些違背諾言透露消息來源的記者。美國法院通常認為,司法訴訟程式應該向公眾和媒體公開,除非另有十分有力的考慮,例如涉及被告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而非秘密審判就無法保證他的這一權利。也許是由於有著對16世紀和17世紀英國"星室法庭"秘密審判的歷史記憶,美國的法官們對秘密審判顧慮重重。最高法院甚至還裁決,州法官有權力自行決定是否允許電視攝像機對庭審過程進行錄影。不過,被告的權利有時候被視為比媒體報導審案情況的權利更重要。例如,為了保護隱私起見,受到犯罪指控的青少年的姓名通常不被透露給媒體。
隨著時代的發展,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美國的法律原則也不斷遇到技術變革的挑戰。美國法院給予報紙等文字媒體的保護往往比給予電視等廣播媒體的保護要更大。例如,最高法院在60年代末期曾裁決,個人不具有利用廣播傳播言論的絕對憲法權利,因為"電磁頻帶"容不下所有人。這個理由成了司法裁決的一個根據,即不承認競選公職的人享有"平等螢屏時間"以對其他候選人在電視上發表過的言論做回應。但是,隨著有線電視以及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近年來的普及,法院看來正趨向於將廣播媒體同文字媒體在法律上一視同仁。
"五角大樓文件"案
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重大的一樁涉及媒體的案件,也許就是所謂的"五角大樓檔"案(The Pentagon Papers)。人們可以從美國政府同美國最著名的報紙《紐約時報》之間的這場糾紛中,對前面討論過的許多有關《第一條修正案》的重大問題略見一斑;而且這個案子還牽涉到近年一個最富爭議性的政治話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行為。
這場糾紛始於1967年。當時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設立了一個專門工作小組,編寫1945至1967年間美國對越政策的歷史。小組由國防部人員和其他政府機關的人員以及若干獨立合同工作者組成。報告中沒有對任何人的採訪;全部研究都是依靠檔進行。最後於1969年脫稿的報告洋洋灑灑,長達7000多頁。它被人稱為"五角大樓文件"。這份文件只印了15份,因為它只是為了供國防部和其他政府機關內部使用。
對編寫這份洋洋大觀的報告有少量參與的合同工作者之一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是從事國防問題研究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工作人員。埃爾斯伯格看到的"五角大樓檔"中的內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使他對美國在越南實行的政策產生懷疑。埃爾斯伯格無法說服國會議員將這份報告公之於眾,於是暗中複製了報告,將其轉給《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五角大樓檔"中幾乎沒有秘密的情報,但是,有若干章節對於美國在捲入東南亞軍事衝突之前和之後採取的對越政策是否明智提出質疑。
1971年6月,在《紐約時報》兩次連載"五角大樓檔"的部份內容以後,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的政府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繼續刊載。紐約的一位聯邦法官下了這一限制令,要求待該案全面聽證後再作定奪。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法院事先制止報紙發表某一具體文章。這是實行預先限制的典型。官司很快就打到了美國最高法院。法院駁回了司法部提出的舉行秘密聽證的要求,使該案在1971年6月26日舉行公開辯論。僅在4天之後,最高法院便做出裁決。六位法官的多數派寫出一項簡短的共同決議(即不署作者名) ,主要內容是,任何要求預先制止出版的申訴,都在憲法上負有重大的舉證之責,而在此案中,尼克森政府未能做到這點。由於組成多數的六位法官各寫各的意見,因此很難看出律師和法學家有時所說的點破司法裁決的核心的"閃光句"。唯一能肯定的一點是,多數法官並不相信,把"五角大樓檔"中的內容公開化會對國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即時的、不可彌補的損害"。大多數憲法專家認為,最高法院就"五角大樓檔"做出的裁決,充其量只是新聞出版自由的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最高法院沒有看到有充份理由制止刊登,但它的確接受了政府的論點,即在預計會拿出出版會造成危害的證據的情況下,可以發佈禁令。該案最後以"五角大樓檔"最終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全國各地其他報紙刊登而告終。沒有因此引起國家安全問題。
監督政府的探照燈
總而言之,媒體一向都在試探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條款的力度,向限制媒體報導政治與社會資訊的企圖發出挑戰,大聲疾呼"公眾有知情權"。這是理所應當的,因為自由的新聞 ─ 即使是偶然越出了良好品味範圍 ─ 對維護民主社會至關重要。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認為這樣的媒體是自由的最佳保證,他情願容忍新聞出版的過份自由,以便通過這種隨時隨刻的審視,把政府的作業置於光天化日之下。
美國熱衷於新聞出版自由的無羈無絆,但並非所有的民主國家都同美國一樣熱衷。實際上,即使是趨向給予媒體越來越多自由的美國法院,也不是始終如一地支持完完全全的言論自由。不過,本文開頭申述的一條原則是:一個要被視為真正民主的國家,就必須準備切實保護媒體的言論自由。美國這方面的歷史記錄儘管並非十全十美,但是,在被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法官1919年稱為的美國憲法理論"試驗"中呈現出的強大趨勢是,讓公開表達思想越來越自由。
相關讀物:
Zechariah Chafee,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Fred W. Friendly, Minnesota Rag: the Dramatic Story of the Landmark Supreme Court Case that Gave New Meaning to Freedom of the Press (Random House, 1981)
Leonard Levy, The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aul L. Murphy, The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Greenwood Publishing, 1972)
Paul L. Murphy, 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S. (W.W. Norton, 1979)
Richard Polenberg, Fighting Faiths: The Abrams Case, the Supreme Court, and Free Speech (Viking Press, 1987)
S.J. Ungar, The Papers & The Papers: An Account of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Battle Over the Pentagon Papers (E.P Dutton, 1972)
---------------------
作者介紹:
約翰? W?詹森(John W. Johnson)自1988年起任北艾奧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他的著作包括:《美國法院的歷史性案件大全》(2001年第2版)、《爭取學生權利:廷克訴得梅因案及20世紀60年代》(1997年)、《防災保險:核工業的官司》(1986年) 以及《美國1908-1940年的法學環境》(1981年)。他目前正著手於一本有關美國生活中的隱私權問題的新作。
眾人皆醒我獨醉
17楼
論民主文集》(9)
利益集團的作用
R? 艾倫?海斯 撰文
"利益集團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標並且努力去影響公共政策的個人組成的團體。"
─ 利益集團協會 傑佛瑞?貝裏
****************
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s)是美國公民用來向民選官員表達他們的想法、需要和見解的一個重要機制。美國公民無論關心的問題是多麼具體或特別,往往都能找到一個專門關注這種問題的團體。從包含美國眾多志願機構的通訊錄上可以看出,公民組成這些社團的原因五花八門。蓋爾調研公司的《社團大全》(The Gale Research, Inc., Encyclopedia of Assciations)被公認為最詳盡齊全的目錄之一。這些社團並不全都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其中有很多以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為目的。
美國政治無論從有形的體制上,還是從無形的傳統上,都為利益集團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美國體制中有利於加強利益集團影響力的特徵之一是,政黨力量相對薄弱,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行政與立法分權的結果。在像英國那樣的議會制中,首相要靠議會中的多數支持來執政,各個政黨對立法議員、進而也就對制定政策,有著相當大的控制力。反之,美國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是兩項分開的政治運作,即使有時候在同時舉行。每個立法議員都必須在他/她的本州或本區結成一個取勝的聯盟陣容,而這種聯盟的性質,同獲勝的總統候選人所組成的多數派聯盟並不一樣。很能說明這一點的現象是,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大部份時間內,國會和總統職權分別掌握在對立的政黨手中。因此,無論是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都不一定非支持本党總統的主張或支持本黨的競選政綱不可。由於對黨派的忠誠度較低,所以,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提高 ─ 這既體現在極為需要經費支援的競選時期;也表現在選舉過後,那些對獲勝候選人提供過支持的利益集團對制定政策的密切參與。
美國體制中有利於加強利益集團影響力的第二個特徵是政治權力分散到州和地方,也就是聯邦制度,或曰"聯邦主義"。公民社團往往是先從州或地方一級產生,然後合併為全國性的組織。權力下放促進了各式各樣的利益集團的產生,而這又進一步弱化政黨體系,因為50個州的社會與經濟情況千差萬別,難以實施絕對的政黨路線。
此外,美國體制中強大、獨立的司法系統也加強了利益集團的勢力。在其他一些民主政體中歸立法或行政機構處理的問題,在美國往往由法院來裁決。因此,利益集團可以通過訴訟來達到無法通過立法途徑實現的決策目標。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在法院的勝訴,給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上打開最早的缺口,比由南方議員控制要職的國會願意採取行動的時間早了好幾年。
最後還有一點:美國對言論、新聞出版與結社自由幾乎毫無限制的傳統意味著,幾乎任何利益集團所表達的觀點,無論多麼激進,都可以有公開傳播的機會。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媒體的日益集中化,使一些持邊緣觀點的團體的聲音較為難以讓人聽到。但是,鑒於各種團體都可以上互聯網,集中化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總之,美國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的傳統,提供了將社會問題公之於眾並就公共政策發表評論的大量機會,從而鼓勵了利益集團的形成。
利益集團的範圍
在1970年以前,美國介紹利益集團的標準教科書大多將它們分為三大類別:工商、勞工和農業。從那時以來,利益集團的範圍已經變得紛繁複雜得多。美國農民人口的減少使農業利益集團失去了影響力,同時,新出現了許多在這些類別以外的新型利益集團。
工商
許多學者一致認為,工商界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一個主要角色。大財團公司在美國經濟中具有顯要地位。由於民選官員要為國家的經濟表現負責,他們往往擔心,如果採取與工商界對立的政策,會有損於經濟表現。
然而,工商界也動用其直接的影響力。大型跨國公司以其巨額資財來推動自己的政治目標。它們通常是多個行業聯合會的成員,這些聯合會代表了整個行業在政治進程中的主張。這些公司也支持著"傘式"聯合性機構,如代表整個工商界聲音的全國製造商協會(Assoc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另外,也有公司單獨直接向議員遊說,拿出數百萬計美元作為競選捐款,支持它們贊成的候選人。
工會
工會在20世紀初發展得很緩慢,但是30年代時在美國政治制度中取得了重要位置。《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保護集體談判,並使工會得以發展得更為迅速。到20世紀50年代,工會會員人數達到頂峰,占勞工總人數的35%。但是,自60年代起,工會會員開始減少,到目前僅占勞工人口的15%左右,工會的政治實力也隨著其經濟實力的減弱而下降。工會會員人數減少的原因十分複雜,在此難以詳細探討,但大體上是由於全球經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美國從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轉為著重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不過,當工會將其能量集中於一個選舉或一個問題上時,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職業社團
另一類重要的利益集團是專業人員的社團。這些團體,如美國醫學學會(Amercian Medical Association)和美國律師協會(Amercian Bar Association)等,專注於自身專業的共同利益、價值觀和地位。勢力稍弱但組織程度並不遜色的是公共部門的專業人員。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幾乎每一專業都有自己的全國性組織。例如,在住房政策領域,有全國住房與再開發公務員協會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and Redevelopment Officials)、州住房機關全國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Housing Agencies)和大型公共住房管理機構理事會(Council of Larg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根據州與聯邦法律,這些團體不得參與黨派活動。但是,當遇到涉及自己工作專案的問題時,這些團體會到國會作證,它們還組織自己的會員同來自本州和本區的議員對話。由於公共專案的服務物件是低收入者,而這些人很少組成具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利益團體,因此,這些公共服務人員的社團就成了美國政治進程中替窮人說話的重要代言人。
政府間組織
另一個有關類別的利益集團,是那些代表州與地方政府不同單位的團體,它們為在全國範圍內爭取自己的利益而遊說。在把權力分散到聯邦、州與地方政府各級的美國聯邦制度中,這些團體並不具有正規角色,但是,它們具有和其他利益集團相同的作用,即將自己成員的看法告知國會和行政當局,並在媒體上宣揚自己的觀點。例如,全國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和全國州議會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代表著州的官員。由於州長肩負著實施聯邦要求的社會福利項目的直接行政和政治責任,因此,全國州長協會在幫助國會議員制訂社會福利法規方面,尤其具有影響力。各縣級機構的利益則由全國縣級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代表,城市的利益由全國城市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和美國市長會議(U.S. Conference of Mayors)代表。
公共利益集團
自1970年以來,發展得最為迅速的利益集團是"公共利益集團"。政治學家傑佛瑞?貝裏(Jeffrey Berry)給公共利益集團下的定義是:所主張的目標並非針對本團體成員的直接物質利益,而是表達其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利益集團。最早的一批公共利益團體是隨著60年代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應運而生的。支持這些事業的人們往往經歷了一段發展過程,從通過街頭抗議表達自己的主張轉到政治體制中進行有組織的行動。後來,公共利益集團又發展到一些新的領域,如殘疾人權利、防止虐待兒童或家庭暴力、男女同性戀權利等。這些團體也是提倡建立扶助窮人的項目的主要力量。公共利益集團中的一些主要團體包括:全國低收入住房聯合會聯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保護兒童基金會(Children's Defense Fund),以及由消費者利益活動人士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領導的社會公民(Public Citizen)等等。
公共利益集團一般缺少工商利益集團那樣的財力。儘管從民意測驗來看,它們的主張往往得到相當大的公眾支援,但是其成員人數一般不多。原因之一是,它們的目標不帶有具體實際利益性質,因而造成"搭便車"的現象,即人們可以從這些團體的努力中獲益,但是自己卻不必成為它們的成員,或者至少不必大力參與。儘管如此,這些團體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並且通過大力的資訊收集,能夠提出其他團體涉及不到的問題。最初,大多數公共利益團體是政治上的左傾派。但是,近年來,保守派也組織了自己的利益團體,大都是為了對付所謂60、70年代公共政策中出現的自由主義傾向。這一類的公共利益團體主要包括:全國納稅人聯盟(National Taxpayers' Union)和婦女關心美國組織(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像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這種的保守派智囊團,也可以發揮利益集團的作用,因為它們的研究傾向于為保守派世界觀提供依據。自由派方面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也許情況與此相仿。
這些國內的公共利益集團,與80年代以來在國際舞臺上湧現的非政府組織(NGOs)相似。實際上,美國的某些團體同國際非政府組織有著密切聯繫。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際的公共利益團體的支持,都是來自關心整體社會問題而非眼前經濟利益的公民。
利益集團效力的局限性
從上述簡短的介紹可以看出,美國政治舞臺上有多種多樣的利益集團;大量的調查研究顯示,這些利益集團宣傳其成員觀點的效力大不相同。造成差異的原因,在於一個團體如何使用自己主要的政治資源,即成員人數、凝聚力/力度、經費、資訊。
成員的人數及其凝聚力
按理說,享有很高支持率的利益集團應該具有最大的影響力。民選官員所宣導的,是在民意測驗中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因為他們希望大批支持這些主張的人有朝一日會加入使他們競選成功的選民陣營中來。然而,有幾個因素使情形變得不是這樣簡單。
不錯,有成千上萬的公民是利益團體的成員,而且有些團體,像環境保護人士組織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和勞工組織勞聯/產聯(AFL/CIO),是相當人多勢眾的。但是,若進一步仔細觀察就可看出,大多數會員眾多的利益集團其實只得到了他們潛在的支持者當中的很小一部份人。例如,民意測驗表明,極大多數美國人贊成實行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這些支持者可以成為環境保護利益集團數百萬成員的來源。然而,即使那些最大的環境保護集團所公開的成員人數,也都不足一百萬。這種相對少的成員人數顯示了這樣一個規律,即參加利益集團的公民人數只占美國人口的很小一部份。
已故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對此做了最為可行的解釋。他認為,一個利益集團實現的某一政策目標,從經濟學上來說,是一種"公共財富"。也就是說,這個團體的成功使那些贊同它的主張的人們都能受益,無論他們是否實際加入了該組織。例如,如果鯨魚得免滅絕,即使從未向"拯救鯨類"團體繳納過會費的人,也可以因為鯨魚的生存而感到快慰。當然,如果誰都不出資金,這個團體是不會存在的。不過,在那些大型利益集團裏,每個新加入的成員所分攤繳納的會費,數額很小。所以,一方面有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加入利益團體,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不加入,或者不完全參與,他們成為所謂的"搭便車者",也就是說,讓別人積極參加並出錢,而自己則坐享其成。
會員眾多的利益集團面臨的另一主要問題是,如何將公民對這個團體的支持轉化為選票,投給那些贊同這個團體的目標的政治候選人?選舉投票是一項複雜的行為,包含著多方面的動機和影響:候選人的個人人品,黨派忠誠度,以及多種多樣的議題。對選舉的研究表明,許多選民對於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究竟持何種政策主張,不甚瞭解。因此,利益集團往往很難證明,它的支持者在選舉中做出的選擇,與該組織的目標相關。那些能夠讓候選人相信其選票實力的團體,是受到敬畏的。例如,反對制訂槍支管制法的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使國會議員確信,這個問題是該會會員給他們投贊成或反對票的關鍵。這樣,全國步槍協會所具有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其會員人數代表的比例,儘管大多數美國人贊成制訂更為嚴格的槍支管制法。
由於動員起大批會員是件困難的事,因此,毫不奇怪,規模較小但卻整齊劃一並且情感強烈的團體,往往能夠產生比其成員人數顯示的力量要大得多的影響力。首先,團體越小,每個會員所繳納的會費就越高,"搭便車者"減少。其次,直到互聯網興起之前,規模越小的團體,成員間的交往聯絡越方便,因此集體行動起來也就容易得多。規模較小的團體的這些優勢,如果再加上其成員與決策結果利害攸關,那麼,即使小團體,也可以變得力量非常強大。
經費
近年來,由於政治競選費用增加,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限制競選捐款的現行法律存在漏洞,而兩黨的許多民選官員不願意支持對現行制度做出修改,擔心修改會讓對方得到好處。那些在全國性選舉中影響力最大的利益集團,往往向候選人提供自願捐款,總額可達數十萬美元。
另外,如果要在非選舉時期在華盛頓保持一席立足之地,也需要有相當大的財力。一個團體需要有一批專業人員去對涉及其利益的立法活動施加影響,還需要一批人員同它自身的成員保持聯繫,並向成員提供服務。利益集團如果不能穩定地存在於華盛頓,就無法對立法過程的細節施加幕後影響,而這種影響恰恰是利益集團成功的標誌。
經費因素也同團體成員和凝聚力等因素相互作用。要克服搭便車的問題,利益集團必須吸引"政策企業家" ,即那些靠辦起成功的利益集團而在物質上、職業上或意識形態上獲得回報的人。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團體需要其未來的成員,作為一個整體,有足夠的財力資源,從而使這個組織有希望發展起來。這種需要形成了一條最低收入的底線,低於這條底線,就難以組織起來。由於這個原因,直接代表窮人的利益集團為數較少。
然而,高出這條底線,財力所起的作用變得更為複雜化。按理說,一個擁有100萬會員、每人繳納5美元的利益集團所籌到的經費(500萬美元),應該與一個擁有會員1萬人、但每人繳納500美元的利益集團所籌到的經費相等。但是,一旦考慮到搭便車問題以及同眾多會員通訊聯絡的高昂費用,人們便可以看出規模較大的利益集團的實際劣勢。
另一個對利益集團調動資源產生影響的因素,涉及它的成員是個體公民,還是其他機構團體。許多勢力雄厚的利益集團,其實是由若干團體組成的團體。它們包括行業社團、職業協會和代表公共與非營利服務設施的團體。一個由有關組織組成的利益集團,不需要動員聯絡很多成員團體,但卻可以稱自己代表著與這些團體相關的成千上萬名成員。此外,它的各個團體會員可以用自己的組織資源,而不是個人的財力資源,提供支援。
信息
除了有忠實的成員和經費以外,資訊是利益集團所擁有的最強大資源。資訊交流通過幾條管道進行。首先,資訊從利益集團傳遞給決策人。利益集團往往具有議員們所缺乏的專業知識,這些團體很熱衷於幫助議員們理解本團體所關心的問題。不錯,利益團體所提供的資訊通常會帶有促進其自身利益的偏見;議員們非常清楚這種情況。但是,他們可能仍然認為這些資訊是有用的。利益集團常駐華盛頓的一個主要好處,就是能有機會在決策過程的關鍵階段向議員們提供資訊。
第二,資訊從立法和行政部門傳遞給向利益集團。這些團體的工作人員隨時跟蹤有關立法提案,從而掌握對立法進程施加影響的最佳時機。通過與國會工作人員的非正式交往,他們有機會到聽證會上作證,並且在接近某項關鍵性投票時,將本團體的成員動員起來。通過這個過程,他們瞭解到哪些決策人士的力量最雄厚,以及用什麼策略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援。有時候,這些團體能使在國會審議中的某個法案的具體文字得到更改,從而影響其產生的效果。
第三,利益集團同自己的成員和其他公民交流資訊。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它所開展或是委託開展的調查,渲染某一個問題。如果媒體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議員們就會感到必須做出反響。這些團體也向自己的成員徵求資訊,並向他們通報即將做出的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為數很少的個體公民會為某項立法找到自己的議員。所以,一個利益集團只要發動寄出200封信,就會令人感到郵件猶如雪片般飛來。
近五年來,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大大降低了聯繫大量民眾的費用。許多利益集團現在都有網頁,許多團體使電子郵件成為自身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決策人之間交流的手段。不過,這種媒介手段還很新穎,這些團體尚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對它加以利用,因此,要確切知道它對利益集團的影響力究竟會產生多大作用,眼下為時尚早。
新近的一個有關這種影響力的例子是,若干保守派的網站被用來傳播有關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負面資訊,其中有些屬實,有些則屬於嚴重歪曲或捏造。這也許對保持彈劾克林頓一案的勢頭起了作用,儘管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反對彈劾。除非大公司想出一個對使用互聯網施加控制的辦法,進而提高上網費用,否則這一新型媒介很可能將起到使政治對話大眾化的作用。反過來,互聯網也有可能促使公民分成許多微小的、靠電子通訊維繫的團體,它們以越來越稀奇古怪的世界觀變得與世隔絕。
讓公共利益集團更有效
由於上述原因,較小、較協調、財力相對雄厚的利益集團的主張,往往比那些代表較多公民的利益集團的主張更容易獲得成功。特殊具體的利益,往往要比那些較籠統的、所謂更大眾化的利益占上風。不過,近年來公共利益集團的大批湧現,的確使利益集團體制在整體上更能體現美國多元化的聲音。而且,公共利益集團經常能夠擊敗看上去更為財雄勢大的對手。可是,歸根到底,民選官員們都懂得,贏得選票需要花錢。在很多情況下,那些有群眾基礎的利益集團無法保證他們的成員會將選票投給候選人,而行業社團和私人公司卻能保證奉獻候選人購買電視廣告所需的美元。
許多公共利益集團的一個重大欠缺,是缺乏真正的基層政治組織。這些團體的典型情況是,有一小批辦事人員,他們依靠數以千計的成員的支持運作,而這些成員同這個團體發生的唯一聯繫,不過是按期交會員費。這種結構同早期的群眾性政治組織完全不同,當時的全國性運動是從較小的、人們面對面交往的地方性組織逐步發展起來的。而現代的這些團體,除了少數積極分子外,成員很少見面。
近年來,美國社會的觀察人士越來越擔心,公民對社區群體事務的參與減少。這種現象既涉及非政治性組織,也涉及政治性組織。人們提出的原因很多:電視帶來的離群效應;雙職工與單親家庭增多所造成的成年人閒暇時間減少;媒體把持的競選宣傳著重於對個人人品和醜聞的大肆渲染,而不注重真正的議題,從而令人們產生玩世不恭的心態。
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公民參與的減少,利益集團如果能夠通過其地方和基層分部有效地將人們動員起來,就會在政治上處於強有力的地位。由於有現成的聯繫管道,它們可以發展起穩定的成員基礎而不必耗費大量的聯絡資金。它們可以通過與候選人和民選官員在地方上的直接接觸,促進在國家層次上的遊說,而且理直氣壯地表示,其成員將把本團體所關心的問題作為投票依據。這將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群眾運動,而不是靠被動的支持者出錢維持的少數管事人員的行動。
然而,創辦這樣一個組織的障礙是十分巨大的。它需要有一大筆創建資金來啟動基層的組織工作。它需要克服美國人將地方性問題同全國性問題分而置之的習慣。它也需要誘導許多公民擺脫那種只知注意全國性媒體提出的問題,而忽視同街坊鄰居面對面交流的傾向。
民主社會的一個標誌,是允許公民發展自己的政治資源;在他們一旦感到,私人公司或政府官員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時,調動這些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發揮著一個根本性的作用 ─ 幫助公民更為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資源:投票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司法程式。
相關讀物:
Frank R. Baumgartner and Beth Leech, Basic Interests: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Jeffrey Berry, Lobbying for the People: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Public Interest Group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Allan J. Cigler and Burdett A. Loomis,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4th 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5)
Michael T. Hayes, Lobbyists and Legislators: A Theory of Political Market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 Allen Hays, Who Speaks for the Poor? 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Policy (Garland Press [forthcoming, 2001])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Basic Books, 1977)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Schocken Books, 1970)
Mark P. Petracca,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 (Westview Press, 1992)
---------------------
作者介紹:
R? 艾倫?海斯(R. Allen Hays)是北艾奧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生專業主任,政治學教授。他的《聯邦政府與城市住房》一書,是有關住房政策歷史的一本受到廣泛引用的讀物。近來,他的研究範圍擴大,研究專題包括,利益集團在制訂公共政策過程中的運作。由勞特列奇在2001年出版的他的《誰替窮人說話?》一書,對利益集團在美國的住房、食品與現金補貼這三個社會政策領域中的活動做出評述和比較。海斯教授到北艾奧華大學任教之前,曾任地方政府的住房主管。
18楼
《論民主文集》(10)
公眾知情權:政府機構的透明度
羅德尼? A?斯莫拉 撰文
"隱瞞政府實情的力量就是摧毀這個政府的力量。"
─ 美國國會眾議院
關於資訊自由的委員會報告(1976年)
****************
"公眾知情權"這句話經常被用作一個政治和法律口號。這些字眼往往同媒體要求獲得政府資訊的呼聲連在一起,是記者在傳播有爭議的資訊時所據的理由。但是,除了新聞出版自由的觀念之外,"公眾知情權"還可以有另一個不同的含義,它完全基於人民的權利,專指公眾有權瞭解自己政府的行為。本文所關注的,正是"公眾知情權"的這一層含義,也就是現在經常被提到的政府的透明度。
政府運作的公開化,增加施政的透明度,往往是一個困難而複雜的過程,需要在各種利益之間謹慎地加以平衡。政府公開化一方面帶來好處 ─ 使政府向人民負責並做到民主參與;但是有時候,政府公開化有著高昂的代價,可能影響到政府內應有的對直言和高效率的追求,或者會危及其他一些寶貴的社會價值,例如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國家安全和執法等。民主政府應該有很大程度的公開和透明度。但是,即使是最公開和民主的政府,在某些情形下,也需要一定程度的隱秘和保密才能合理地運作。
美國為平衡這些不同需要所做的努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問題上:(1) 對公眾開放公共檔案與檔,這些檔案與檔以某種有形的方式記載著"公眾事務";(2)對公眾公開政府的議事機制,如:辯論和決定公共事務的會議或論壇;(3) 對公眾開放政府從事非議事性日常事務的機構,如:政府監獄、醫院、學校等。
資訊自由:對公眾開放檔案與檔
在美國,對"資訊自由"的體驗,即人們體驗到自己享有查閱政府檔案與檔的強大法律權利,是6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一個歷史上比較近期的現象。1967年,針對公眾日益強烈地感到,聯邦法律通常都被用來作為不公開信息的依據,而不是鼓勵將資訊公佈於眾,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通常稱為FOIA)。《資訊自由法》規定了一條總原則,即將把官方資訊對公眾開放,供公眾審閱。這是常規,是"涵蓋性的"規則,美國的法庭一再強調,根據《資訊自由法》,聯邦機構必須對公民提出的獲取資訊的要求做出迅速認真的反應。
《資訊自由法》規定了可以被免於強制公開的九種例外情況。它們是法律所允許的僅有例外,其目的完全是為了確立用來判斷某一材料是否可以不被公開、還是必須被公開的具體標準。如果某一機構以其中某一例外情況為理由拒絕公開材料,遭到拒絕的公民可以從法庭得到迅速救助。法庭一旦認為該機構沒有理由不公開這些材料,就會下令將其公開,並且有可能對該機構處以罰款。
制訂《資訊自由法》的目的很廣泛,為的是使公眾能夠得到被不必要地長期封閉的官方資料,力求建立起可以通過司法手段實現的公眾權利,讓公眾從可能不情願公開信息的官員手中得到資訊。《資訊自由法》列出九種例外情況是為了提供一個有效的公式,將所有各方的利益相容、平衡、保護;但這項法律所強調的是,讓資訊得到最充份的負責任的公開。可以得到豁免的這九種例外情況是:
(1) 涉及國防或對外政策的國家安全機密;
(2) 純粹涉及某一機構內部人事規則與慣例的材料;
(3) 被其他聯邦法律專門規定不予公開的資料;
(4) 貿易機密與專屬或保密的商業與金融資訊;
(5) 凡是沒有被法律要求向任何方面公開的機構與機構之間或機構內部的備忘錄或信件 ─ 在訴訟案中依據法律需向另一方公開的情形除外;
(6) 一旦公開將使個人隱私遭到明顯不正當侵犯的人事與醫療檔案或類似檔案;
(7) 為執法需要而彙集的檔案或資訊,但其不公開的程度以下列情況為限:根據合理的預計,這些執法檔案或資訊一旦被公開將干擾執法程式;將使某人無法享有獲得公正審判或公平判決的權利;根據合理的預計,將構成對個人隱私不正當的侵犯;或根據合理的預計,將會暴露保密資訊來源的身份。對於執法當局在刑事偵查過程中或是某一機構在國家安全情報調查過程中彙集的資訊,《資訊自由法》規定,在如下情況下不予公開:如果由保密資訊來源提供的資訊一旦公開將暴露執法調查或檢控所用手段與程式,或者暴露執法調查或檢控所依循的指導方針,而根據合理預計,一旦暴露這一資訊,有可能導致規避法律的情形或危及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
(8)與對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審查及規定有關的資料;
(9) 涉及水井的地質與地球物理資訊與資料,包括地圖。
上述豁免情形,有些要求我們必須在一些重大的相互影響的政策考慮中做出平衡;另一些則涉及相對具體的、適用面較窄的情況,例如:水井位置或是銀行的規定。實施《資訊自由法》所引起的三大主要政策性辯論和訴訟涉及:對國家安全和國防事務資訊的豁免、對有關執法資訊的豁免,以及旨在保護個人隱私的豁免。
公開施政和尊重隱私這兩種價值觀的矛盾尤為突出。特別是隨著現代電子資訊檔案的發展,當代社會中幾乎沒有人能將有關自己的許多情況完全保密。許多有關個人的資料由於合理的原因而到了政府機構手中,儲存在政府控制的資訊檔案中。因此,如果要對隱私給予任何有意義的保護就必須認識到,儘管在現代社會裏不可能做到完全保守秘密,但是仍然有可能制訂法律,確保資訊的公開要經過嚴格甄別,這樣的法律至少可以為做到對個人隱私給予某些保護發揮很大作用。
除了聯邦《資訊自由法》以外,各州也有不同的關於資訊自由的法律。美國所有各州都有州法律,讓公眾能夠獲得州和地方政府的檔案資料。這些法律因州而異。許多州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資訊自由法》的模式,首先規定政府資料必須對公眾開放的普遍原則,然後再定出例外。
實施資訊自由法律給國家和地方帶來的費用,長期以來一直是公眾激烈爭論的問題。按照《資訊自由法》提出的索取資訊要求的一部份直接費用,通常由索取人承擔 ─ 例如檢索費與複印費之類的收費,都列在由各機構負責的統一收費價目表上。但是,《資訊自由法》的間接費用,也可說是"資訊公開的行政開銷",很多都由各機構作為其運作經費的一部份承擔下來。資訊自由無疑使得政府開支更大,因為一個機構若要對按照《資訊自由法》提出的查閱要求做出應有的回應,就必須雇用政府雇員來編目、歸類、儲存以及提取資料,形成一整套管理機制。
美國人現在懂得,將自由價值觀付諸正式法律是一回事,而設法改變政府的作風,使官員們遵奉政務公開的精神,努力便利公眾得到公共檔案而不是阻撓和破壞這種公開性,卻又是另一回事。《資訊自由法》剛生效的頭幾年,許多機構把這項法律視為麻煩,儘量予以回避。但是,人們的態度逐漸發生轉變,新一代政府官員顯得更為開放,更能接受讓公眾方便大量地查閱公共檔案的觀念。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施政作風的改變歸功於20世紀90年代的電腦新技術。網際網路本來同查閱政府資訊資料毫無關聯,但是,它形成了一種"資訊文化",讓全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越來越習慣於通過自己的電腦,迅速而廉價地獲取包羅萬象的資訊。全世界整個一代人都在開始把通過網際網路輕易獲取資訊看作是一種天經地義的權利,猶如呼吸周圍的空氣一樣自然。在各民主國家,人們自然而然地將這種權利感引伸到對政府的關係上。使做到使政府檔案易於上網查閱越來越被視為民主政府的基本義務之一。因此,公民現在所期待的不僅是資訊自由,而且是網上資訊自由。這個日益普遍的意識後來反映到美國聯邦法律中 ─ 1996年,國會通過了《電子資訊自由法》,明文規定,"公共檔案"的概念包括以電子形式儲存的檔案,並要求聯邦機構允許通過電子方式查閱其檔案。
隨著網際網路的成熟並成為大眾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幾乎所有民間企業和組織都紛紛製作了網頁,提供充實的資訊和網上互動機會,政府也受到壓力,必須參與電子市場的競爭,使自己也變得"網際網路服務友善"。在國家和地方層次,政府機構在日益擴充網上資料庫,使公共檔案便於任何一位元擁有電腦與數據機的公民查閱。最終,這將可以解決由資訊自由法帶來的費用問題。由於政府資料常常採用電子形式,政府機構或許會看到,只需使用一些軟體,方便上網普通公民識別和提取資訊,那麼,向公眾公開公共檔案資料的工作是相對容易的。
對公眾公開政府的議事機制
施政的公開透明,不僅涉及政府的檔案資料,而且也關係到政府的決策過程本身。美國有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憲法》保護的強大傳統,保障公民有權瞭解法庭與立法機構的議事內容和過程。近年來通過的一些俗稱"陽光法"(sunshine laws)的聯邦與州法律,進一步保證公眾有權知道行政與管理機構會議的內容,從而進一步擴充了這一傳統。
美國最高法院於1980年在對"里士滿報業公司訴弗吉尼亞州案"(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 Virginia)的裁決中說,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中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包含公眾瞭解刑事審判案的權利。這個權利的主要意義是,它認識到,公眾對刑事審判程式的瞭解對社區民主生活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Burger)在他做出的代表法官多數意見的闡述中說:"公開審判(在美洲殖民地時期)的早期歷史,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早在行為科學專家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普遍認識到,公開審判對社區有極大的安撫效用。雖然當時還沒有專家將這種認識著書立說,但是,人們通過經驗和觀察感覺到,為了正義而採取的手段必須有賴於公眾對程式和結果都給予的認可,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尤其是這樣。"美國許多法庭還將這一旁聽刑事案的權利擴大到民事案。的確,將知情權用於民事案有著基於歷史和功能的強有力的理由。正如19世紀的最高法院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經指出的,民事司法程式向公眾公開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公開化對正當司法審理的保障……。將(民事)案件審判置於公眾目光下進行之所以可取,並不是因為某一公民同另一公民之間的紛爭與公眾有關,而是因為審判人時刻都應本著對公眾的責任感行事、以及每個公民都應能親眼目睹公共職責履行的方式是極其重要的。"
在當今的電視時代,公眾旁聽司法審判程式的權利隨著美國一個日益流行的做法而更加擴大了,這就是,允許電視攝像機錄拍攝法庭的申案過程。目前,美國法院還沒有確認電視攝像機進入法庭屬於憲法賦予的權利,但是,許多法院通過州法規或經地方法院裁決,如今經常允許電視攝像機拍攝和報導審案過程。實際上,美國有一個有線電視網,叫作"法庭電視"(Court TV),它的主要節目就是逐日、逐小時地播放審案實況。目前,知情權在美國州法院得到比在聯邦法院更普遍的運用。
美國最高法院不允許在其法庭內設置攝像機或進行電臺現場直播。近年來,最高法院將其會議記錄錄音,待下一審案期開始時,通過國家檔案館予以公開。2000年,最高法院在對受到高度關注的總統大選訴訟案進行審議時,曾允許新聞媒體在會議結束後立即播放會議的全部錄音,以滿足公眾的強烈企盼。這樣,美國人得以在聽證結束後的幾分鐘內,立即聽到長達約90分鐘的聽證情況。
凡是在攝像機或麥克風被允許進入法庭的情況下,法官通常擁有相當大的設立基本規則和程式的決定權,以便將攝像機和麥克風的影響減至最低限度,並保證它們的存在不會給最至關重要的公平審判打折扣。
在立法層次,美國議會有著公開辯論的悠久傳統。這通常並不是由於有憲法檔給予的保證,而是基於對立法機構自行決定的信任。無論怎樣說,美國國會和州立法議會將議事過程向公眾公開是一個悠久的傳統。近年來,各立法機構的開會情況已經成為日常的電視內容。在美國,C-Span電視網定時播放國會的開會情況;州立法議會的開會情況現在有時也得到轉播。
面對人們普遍認為,就對公共事務的實際管理而言,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機構的會議往往比立法機構的辯論更加重要,聯邦政府和許多州政府開始實施會議公開法(open-meetings laws),也常被稱為"陽光法"。
聯邦會議公開法,即《陽光政務法》(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於1976年由國會通過。該法要求將聯邦機構的會議向公眾公開。該法對"會議"的定義是,至少是由代表機構辦理公務的該機構官員所進行的商議。《陽光政務法》規定,除非是在這種公開會議上,否則官員不得"共同展開或處理機構公務",並且進一步申明,"機構每一次會議的每一部份都將公開,讓公眾觀察。"
可以料想,對這項法律也有例外情況。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與《資訊自由法》中的例外規定相應,即涉及國防或對外政策、機構內部條例、貿易機密、執法調查、金融機構規定、個人隱私、以及傳票、訴訟等的會議內容,可被免于執行《陽光政務法》的公開要求。
陽光法的關鍵在於"會議"這個概念。該法設法加以區別的是:機構內部有關人員進行的將做出對公眾有影響的決定的正式會議,和實行管理所必需的、自然的、必然的、初步和非正式的對政策的磋商。國會在起草《陽光政務法》、為"會議"的概念下定義時懂得,不可能將行政管理過程完全置於眾目睽睽之下。為澄清問題和闡明不同看法而進行的非正式的背景磋商,是政府機構工作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份。妨礙這樣的磋商,就會影響到官員之間的開誠佈公,拖政府工作的後腿,對公眾不會有益。因此,為做到平衡,這項法律只適用于機構人員展開或處理該機構的正式公務的情況。
電視再次推進了這一法律實踐。在美國各地,地方的有線電視系統通常都另辟一兩個頻道,完全用來播送地方政府會議 ─ 如市或縣政府例會、校董會會議或城建規劃委員會會議等。
機構開放
自由社會的公民,包括媒體人員,究竟應該享有多大的法律權利進入像監獄或學校這種政府管理的公共機構?
對這個問題可以做出的一個回答是,公民根本就不能進入政府的設施,因為那畢竟是屬於政府的財產,政府應該有權決定讓什麼人或不讓什麼人進入。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被美國法律否定。根據體現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原則的"公眾講壇法",某些場所,如公園、大型公共廣場、街道、人行道,被視為"傳統的公共講壇",是為人民代管的政府財產,也就是說,在這些場所,公眾仍然有為和平表達意見而集會和示威的權利,只要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美國法院還確認,某些其他設施,如公共禮堂、會議室、大型公共建築的門廳,也都可以成為"公共講壇",任何人都有權利在那裏宣講或聆聽。
但是,許多政府機構並不是適合發表言論的"公開場地",而是處理政府日常事務的辦事機構。這些事務並不是指公共有權參加的政府議事或決策事務,如法院和行政機構會議,而是指政府的另外一些非議事性職能,如公立醫院、學校或監獄。這些機構在傳統上不被視為"公共講壇",不存在公民進入這些設施的傳統權利,進入這些地方的人往往要與其公務有關。例如:學校可能只允許學生、教師、管理人員和家長進入;醫院可能只允許患者、醫務人員和探視人進入;監獄可能只允許囚犯、獄監和律師進入。
但是,所有這些機構,以及可以想像得到的其他許多機構,都可能受到來自公民 ─ 包括媒體人員的壓力,要求得到進入的權利,以便觀察和評斷那裏的情況。一些公眾或媒體中的成員可能想報導這些機構中傳出的問題,如虐待、腐敗、惡劣條件或是其他被認為不合理的情況。鑒於這些機構的經費來自民眾,人們認為,公眾有權知道其內部的情形。至少就目前來說,美國法院還不願確認依據《憲法》有任何普遍適用於進入這類機構的權利。不過,有些法庭願意確認一項不歧視原則,即如果這些機構讓公眾有某些知情的權利 ─ 如公眾參觀監獄的權利, 那麼,它們就不能對媒體或者對專門為觀察和收集這些機構可能存在的問題而前來參觀的公民加以歧視。
開放的價值
世界自古至今所有地方的所有政府,都有將其運作保密的本能傾向,至少是希望有部份程度的保密。這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是政府的自然本性。因此,如果一個社會認真地希望把開放作為一種價值來對待,就必須制定一些刻意有助於開放的規則 ─ 甚至做到表面看來有些過份的程度,以便對應政府要控制、要檢查、要保密的固有傾向。
今天,通訊業突飛猛進,帶來了猶如當年印刷機誕生時的那種技術革命;這些發展勢必大大改變我們收集、儲存、組織與傳送資訊的方式。一個致力於社會開放的國家,將捍衛對人性與良知的多采多姿的表達方式,並且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和平群眾抗議自由提供切實的保護。這些自由之所及將不止於政治言論,而是包括令人類的想像力展翅翱翔的對藝術、科學、宗教、哲學等浩瀚無際的各種領域的探討。
一個希望將開放視為具有決定性重要價值的社會,將不僅讓公民享有廣泛的個人言論自由,而且還會更進一步,將政府自身的議事過程置於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公眾審查。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的常規是,政府不閉門辦公。立法、行政與司法程式都例行地向公眾公開。
相關讀物:
Ellen Alderman and Caroline Kennedy, The Right to Privacy (Knopf 1995)
How to Use the Feder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6th ed., FOI Service Center)
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Harvard 1983)
Rodney A. Smolla, Free Speech in an Open Society (Knopf, 1992)
Sanford Unger, The Paper & the Papers: An Account of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Battle over the Pentagon Papers (E.P. Dutton 1972)
---------------------
作者介紹:
羅德尼? A?斯莫拉(Rodney A. Smolla)是里士滿大學法學院艾倫贈款專聘教授。他是擅長憲法學的學者、作者、律師。
13楼
《論民主文集》(11)
保護少數族群權利
廷斯利?亞伯勒 撰文
"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孩子將生活在一個
不是根據膚色而根據內在品格來衡量他們的國度裏。"
─ 小馬丁?路德?金博士
1963年8月在華盛頓遊行集會上的演說
****************
美國《憲法》起草人將奴隸問題留給後代人解決,而南北戰爭和重建時期(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僅僅使昔日對奴隸及其子女的種族歧視得到暫時緩解。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最高法院開始對那些以種族、膚色和祖籍為由實行歧視的法律給予嚴格審視,禁止政府制度中的幾乎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
國會也開始制訂法律,禁止在投票、就業、公共設施、住房以及聯邦資助項目等公共與私人活動領域中實行種族歧視。其後,最高法院也對那些基於性別的法律予以仔細審查,而國會則不僅在各種領域禁止性別歧視,而且也禁止以殘疾為由的不平等待遇。
圍繞擴大平等觀念的辯論是美國歷史上最痛苦、然而也最為深刻的一部份經歷。也許除了那些最為同一化的社會以外,公正對待少數族群是一個國家所面臨的最根本、也是最艱難的責任之一。一個社會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地對待每一個人。政府經常不得不在法律上做出劃分,將人們分為不同的群體,對某一群體的人比對另一群體的人給予或多或少的優惠。稅率依收入水準高低而有別,投票或取得駕駛執照都必須達到一個基本年齡 ─ 這些都是這類法規的常見例子。只要是為了合法和重要的社會利益,這種分類被視為是合情理的,有理由期待公民予以服從。
反之,那些把人們根據種族、原籍國家、族裔、性別、宗教信仰或類似的因素加以區別對待的政策,在理智的人們看來,是與施政目的根本不相干的。政府如果出於對天生的特點的考慮,或者出於與人們是否享有福利或承擔責任無甚關係的理由而給予某些人不平等的待遇,那麼,人們就會懷疑,有關官員的做法完全是出於對個人價值與行為的偏見和成見,而不是追求明確合法的公共目的。
但是,在這些原則之外,劃分族群的方式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被視為不公正因而受到譴責,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態度。如果一個群體是社會人口中的少數,具有其他人覺得奇怪彆扭的明顯外在特徵或生活方式,曾經長期受到由政府認可的種種資格限制,或是信奉非正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與習俗,那麼,要實行改變,會遇到社會很大的阻力,要他們完全融入社會可能會令人感到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
不公平地對待少數族裔和其他群體的做法,並不限於對法治不太尊重或根本不尊重的專制制度。以英國為例。儘管英國有著致力於民主和公平的悠久傳統,但在20世紀60年代也曾必須面對給非白人移民待遇的問題。此外,圍繞著奴隸制及其殘餘影響的歷史鬥爭,顯然也是美國最為深刻的法律和社會發展經歷。
即使一個國家決定要結束對少數族裔或其他弱勢群體的歧視,也仍然存在著應該採取何種補救措施的問題。反歧視政策究竟是只應該對政府官員有約束力、還是也應該對私人和民間機構有效?是不是制止眼前的歧視就已經足以、還是有必要採取種種辦法,以糾正昔日的不公正所留下的後果 ─ 例如為尋找就業機會、升遷機會、大學入學機會和其他利益的弱勢族群成員提供優惠待遇?總而言之,是否可以把昔日的不平等作為今後的特定權益?如果可以,那麼,這種權益究竟是應該限於那些昔日親身蒙受歧視的個人呢,還是應該惠及某一特定族群的所有成員?
歧視使民主社會蒙受公開恥辱
縱觀美國歷史,它在處理各種各樣的涉及少數族裔和其他弱勢群體的議題時 ─ 從圍繞奴隸制及其遺留問題的痛苦鬥爭,到將平等原則擴大到性別和其他非種族性質的歧視問題;從努力為美國殘疾人確立和保證平等競爭機會,到近年來爭取將個人的性取向納入應受法律保護的隱私權之列 ─ 幾乎總是要面對上述那些問題。
有一些基本主旨一直貫穿在每一次運動中,它們包括:第一,某些形式的歧視是對開放和民主化社會這一觀念的公開侮辱。1963年,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在對全國發表的一次講話中,雄辯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那一天,法院面對主張種族隔離的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反對,下令取消阿拉巴馬大學的種族隔離。總統在當天晚上說,"我希望,每一個美國人,不論他住在哪里,都會為這一事件和其他相關事件而駐足捫心自問。這個國家由來自許多國家與背景的人所創立。立國的原則是人人生而平等,只要有一個人的權利受到威脅,所有人的權利都被削弱。"
隨後,在同一年的夏天,當時最重要的民權運動領袖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通過他的"我有一個夢"的演說,動人心弦地表達出平等運動中的又一基本原則,把在華盛頓的民權大遊行推向高潮。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在簽署《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結束奴隸制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的紀念堂前向20萬人發表的講話中,對將公共政策及私人行為方式基於對人的價值的成見的這種社會不公給予公開譴責。馬丁?路德?金大聲疾呼,"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根據膚色而根據內在品格來衡量他們的國度裏。"
第三,人們對自身利害的實際考慮為少數族裔及其它弱勢群體爭取保護的運動增添了動力和支持。如果一個社會可以任意歧視某一類的人,那麼它怎麼可能防止其他偏見的出現?許多公民們可能認識到,對某一人種、宗教、族裔背景或非正統習俗及取向的人的歧視,有可能導致對其他群體的攻擊。
反對奴隸制的運動
由於有這些擔心,美國逐漸擴大了不為國家所容忍的歧視類別,在司法、立法與行政領域,並且從公眾輿論上,向這些歧視開刀,其中以對奴隸制及其殘餘的鬥爭最為艱難和曠日持久。當20世紀80年代美國慶祝《憲法》誕生200周年時,於1967年被任命的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非洲裔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就曾說過,對他這個種族的人來說,並沒有多少理由要為《憲法》最初的施行拍手慶賀。馬歇爾說,非洲裔美國人,要稱頌就應該稱頌《憲法》的第十三、第十四與第十五條修正案,稱頌南北戰爭與重建時期的那些禁止奴隸制、禁止在投票權及國家生活其他領域中實行歧視的法令。
也許可以說,馬歇爾法官的這番話都很多言之有理之處。畢竟,1787年的《憲法》原文規定,在確定各州人口數量以便決定該州在國會眾議院的代表人數時,將奴隸按五分之三個人計算。《憲法》還包括了一項條款,在1808年前一直禁止制訂任何針對限制輸入奴隸的法律修正案,而且還保證奴隸主可以追回逃亡的奴隸,甚至是那些已經跑到奴隸制被定為非法的州的奴隸。而且,直到美國圍繞奴隸制和有關問題爆發南北流血戰爭的前夕,最高法院還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訴桑德福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裁決,非洲裔美國人,無論是自由人還是奴隸,都不是美國公民;他們也不享有《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
南北戰爭後,由國會通過並經各州批准了一系列《憲法》修正案,旨在保障那些在戰爭時期已被林肯總統1863年的《解放宣言》解放的前奴隸享有完全的公民權。1868年批准的《第十四條修正案》的一個關鍵規定是:"任何一州不得制定或實施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任何一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拒絕給予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護。"
重建時期的這些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及其早期的施行,只是局部和暫時地在美國結束了對少數族群的歧視。國會根據它所具有的實施修正案的權力,通過了若干重大的民權法規。例如1875年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禁止在公共交通、旅館、影劇院中實行種族隔離或歧視。但是,即使是曾經通過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國會仍然准許在國家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學校中實行種族隔離。而且,到了19世紀70和80年代,隨著全國重建熱情的平息,最高法院對國會原先通過的這些民權法律或做出狹義的解釋,或視其為違憲而推翻。
種族隔離法律的興衰
重建時期後的最高法院還給一些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律予以袒護認可。在審理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時,最高法院支持各州有權要求在火車和其他公共和私人場所實行種族隔離,只要被隔離的設施"相等"即可。最高法院的多數法官的結論是,規定種族隔離的法律對黑人和白人產生同等的影響,沒有給任何一方打上低等的烙印。州還可以有理由確定,這些法律是促進公共安定秩序所必需的。
唯一表示異議的最高法院法官是曾經身為肯塔基州奴隸主的約翰?馬歇爾?哈倫(John Marshall Harlan)。他駁斥了大多數法官所認為的種族隔離法律對占統治地位的白人和對從前的奴隸一視同仁的觀點。他在自己的裁決意見中指出,按照重建時期的那些修正案,"我們的《憲法》是不區分膚色的,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公民中的等級。就民權來說,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哈倫預言,最高法院如此袒護各州,任各州將非洲裔美國人困在半奴隸狀態,"長期下去,其為害之烈,勢必不亞於本法院對'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裁決決定。"
在"普萊西案"之後的半個世紀內,"隔離但平等"論在美國一直被奉為圭臬,種族歧視唯有鬧到最不像話的地步時,才偶爾在法院遭到挫敗。不過,到了20世紀30、40年代,最高法院開始用更為批判的目光來看待種族隔離法律和與此有關的種族歧視行為。最高法院法官哈倫?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在1938年為"合眾國訴卡羅林物產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所寫的裁決理由中,有一個著名的"註腳4",他在其中提出了那些應受到嚴格司法審核的法律,其中包括"對個別和孤立的少數族群的偏見"。雖然最高法院曾以軍事需要為根據維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日裔美國人的制裁,但是法官雨果?L ?布萊克還是代表多數法官強調:"一切針對限制單獨一個族裔的公民權利的法律規定都立即令人生疑。"最高法院在那個時期的一個最重大裁決中,開始逐步清除在研究生教育與職業教育領域中的種族隔離。在對1950年"斯韋特訴佩因特案"(Sweatt v. Painter)的裁決中,法院不僅確定德克薩斯州新創辦的一所專供黑人就讀的法學院比只有白人就讀的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要差,而且還裁定,審案法院在確定隔離的學校條件是否相等時,既要將有形的因素,也要將無形的因素 ─ "那些無法客觀衡量但卻與一所法學院的地位相關的因素(如該校的聲譽)",一併予以考慮。
瑟古德?馬歇爾當時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律師,他和其他一些民權律師在看到最高法院在這件案子上收緊了對"隔離但平等"論的解釋後決定,現在應該是向"隔離但平等"論本身提出挑戰的時候了,尤其是其中所含的隔離設施可以做到平等的假定。經過大量的訟爭,最高法院在1954年5月17日認同了他們的論點。首席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在法院做出的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及其相關案件的一致裁決結論中說,到按照法律隔離的學校就讀,給少數族群的兒童帶來低人一等的感覺,對他們的學習能力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這樣的學校受到的教育絕不是平等的,絕不符合《第十四條修正案》所規定的保證"平等保護"的要求。次年,在第二個一致裁決(Brown II)中,沃論首席法官指令各下級法院和各教育委員會"穩步全速地"實施公立學校的非種族隔離化。
在1969年沃倫首席法官退休之前,最高法院和一些下級法院還推翻了存在於國家生活其他許多領域中的種族隔離方式,其中包括弗吉尼亞州的禁止不同種族的人通婚的法律。在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任期1969-86年)和威廉?H?倫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任期1986年至今)兩位首席法官的先後主持下,最高法院准許各級法院法官在對學校種族隔離問題的訴訟案中具有廣泛的補救措施決定權,其中包括由法院下令用校車接送學生,以保證設在種族隔離居民區內的學校實現種族混合,並且規定了學生中和教職工中的種族比例。但是,最高法院法官對於法律上(即官方)的隔離同既成事實的隔離(即完全是由於住房佈局上的分離而產生的隔離)做出明顯區分,斷定後者沒有受到《憲法》的禁止。另外,大多數法官還指令各審理法院,在將種族雙軌校制轉變為單一校制方面一旦有切實的努力成效,就可將廢除隔離的命令撤銷。最後,最高法院將《第十四條修正案》對"平等保護"的保障局限於判斷政策是否有歧視的意圖,而不僅僅是它是否對種族有不同的影響。
雖然從許多方面來說,美國最高法院對實現種族平等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但是,白宮和國會也為防止種族歧視設立了重要保障。在員警同民權遊行示威者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發生的暴力衝突引起舉國聲討後,甘迺迪政府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民權法律,在甘迺迪總統1963年遇刺身亡後,林登?B?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推動國會通過了這些法律。由國會通過實施的旨在管理州際貿易並貫徹《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的1964年的《民權法》,禁止在公共膳宿設施、就業及聯邦資助專案中實行種族及類似形式的歧視,其中最後一項對於加速取消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起到了比任何法院命令都更為有效的作用。在阿拉巴馬州爭取投票權的遊行示威者遭到暴力襲擊後,國會在1965年實施了《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那些有選民登記歧視歷史的州對選民進行識字測驗及其它選民測驗,並且要求它們在實施新的有關選舉的法律之前,必須經過聯邦官員的"事先許可"("pre-clearance")。1965年的這項法律使南方各州辦理選民登記的非洲裔美國人人數大幅度增加,同時導致在政治角逐中用種族主義討好選民的做法相應減少。而且,國會通過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開始消除大多數住房事務中的歧視現象。
所有少數族群的權利
在美國遭受種族歧視的當然不僅是非洲裔美國人。美國對待土著美國人的歷史是同樣令人遺憾的。許多年來,國會和法院推動向西部擴展,以犧牲印第安人的財產權為代價,沒收了他們的土地,把他們隔離到生活條件往往很差的保留區。
但是,印第安人最終得到了公民權和投票權。而且,自20世紀60年代起,印第安人的民權團體行動起來,爭取到了有關狩獵、捕魚、土地權的一些重大勝利,包括對墓地和其他聖地的保護。但是,在1990年的一個重大案件中,最高法院拒絕對某些部落在儀式中使用佩奧特仙人掌的做法給予有力的保護,法院裁定,宗教行為必須符合不具宗教色彩的刑事法律,包括有關藥物的法規。
多元化的西班牙語裔美國人也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遇到類似的困難。語言障礙以及社會對非法移民,尤其是對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感到的擔心,使西語裔在就業、住房和教育方面很容易成為歧視對象。而且,爭取使英語成為國家正式語言的運動所針對的主要是西班牙語。不過,同美國其他少數族裔群體一樣,西語裔美國人近年來也取得了進展。198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克薩斯州的一項不讓非法移民的無身份子女免費就讀公立學校的政策,法官強調了教育對兒童日後發展的重要性。
儘管以人數而論,美國婦女在全國人口中並不占少數,但是,如同在大多數國家一樣,婦女從傳統上受到很多基於性別的觀念的限制。在1920年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之前,法院常常維護各州不讓婦女有投票權的法律。最早期的若干裁決維護的是那些禁止婦女從事法律、醫藥等職業的規定。甚至到了1961年,最高法院還維護了佛羅里達州的一項法律,這項法律規定,除非婦女特地表示希望擔任陪審團成員,否則排除婦女參與陪審團的工作。然而, 性別幾乎與種族一樣,不屬於政府應該用來決定利益和責任分配的適當理由。婦女像非洲裔美國人一樣,也長期一貫被拒於政治進程之外,因而也就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
基於這些考慮,國會在1964年的《民權法》中,將性別歧視列為被禁止的就業歧視之一。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al Amendments)禁止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歧視女生。在"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和其他一些團體的壓力下,國會於同一年提出《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建立各州立法議會予以批准。這項法案規定,"法律面前的權利平等不應被合眾國或是任何一州基於性別原因而拒絕或削減",並且將執行權授予國會。但是最後,《平等權利修正案》沒有得到足夠數目的州的批准,而最高法院一般拒絕將按性別區分的問題同按種族區分的問題等同而論。不過,1971年,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平等保護"為理由推翻了一項性別歧視的法律。幾年之後,最高法院的多數法官裁定,以性別作基礎的法律屬於"較可疑"的範疇(quasi suspect),故只有當同政府重大的利益有實質的聯繫時,方可維持其效力。由於婦女可以自行懷孕,在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得到承認的有爭議的墮胎權,既被視為一個對個人隱私權的保障,也被許多婦女看作是防止性別歧視的保障。
一般說來,美國一向不太情願對基於性取向的歧視給予禁止,也不願意承認成年人有權在兩相情願的情況下發生同性關係。只有若干城市、縣或州已經禁止用性取向作為分類標準,其中有些甚至承認了同性戀婚姻。在1996年的"羅默訴埃文斯案"(Romer v. Evans)中,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數,基於平等保護的理由,推翻了一項州憲法修正案,這項修正案要禁止在現在和將來制訂保護個人不因其性取向而遭到歧視的任何法規。雖然最高法院拒絕將同性戀者宣佈為一個受特殊保護的群體,但它譴責該修正案是一個州要將同性戀者貶為二等公民的、不能被允許的嘗試。
1971年,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宣佈,外僑身份,即作為非法移民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憲法上的可靠性,並且保證要對那些把美國公民和非公民區別對待的法律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核。日後的一些裁決推翻了只讓公民享有公共福利待遇的若干法律。同時,法官們明確表示,聯邦當局將公民同外籍居民加以區別的措施,在執行中應優先於州當局採取的措施。法官們還確認,在對公民與非公民待遇一視同仁這個總規則下存在例外,維持了若干關於只允許公民擔任公職的法規。
鑒於一般來說年齡的增長同工作職責表現相互關聯,最高法院拒絕將與就業有關的年齡分類列入法律上的"較可疑"之列。但是,毫不奇怪,隨著老齡人的政治影響的日益增加,國會實施了若干防範年齡歧視的法規。例如1964年的《民權法》就將年齡列入幾種被禁止的就業歧視方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退伍軍人和美國的其他殘疾人向國會進行遊說,要求得到保護,不因殘疾而遭受歧視。1990年,一個致力於這項立法的聯盟說服國會通過了《美國殘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這項法律將殘疾人的概念定為肢體或精神上的損傷導致一種或多種"生活活動"受限制的人,它保證讓符合這一定義的所有殘疾人能夠使用公共設施、得到就業機會、享用通訊服務,同時要求雇主和其他方面必須做出必要的調整,以便達到法律的要求。《美國殘疾人法》對於減少殘疾人在就業、教育及其它場合中所遇到的障礙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最高法院有若干裁決對該法的規定做出了狹義的解釋。例如:在1992年的一個案子中,大多數法官裁決,《美國殘疾人法》沒有一定要求航空公司雇用視力近視的飛行駕駛員,即使其視力能夠得到矯正。
有關反歧視行動的辯論
伯格和倫奎斯特先後主持的最高法院還遇到一個沃倫主持時期未曾遇到過的有關歧視的問題,即圍繞"反歧視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激烈糾紛。為了扭轉昔日在就業和高等教育領域對少數族群和婦女的偏見所造成的影響,政府機關和大學自20世紀60年代起陸續設立了一些項目,在錄取、雇用和晉升方面向少數族群和婦女提供不同程度的優惠。支持這些項目的人聲稱,這是一種臨時措施,為的是保證那些在歷史上受到蓄意歧視的族群的成員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並且加速形成一個真正融合的社會。他們還強調,雖然作為這些項目的所謂受害者的白人指責這是"反向歧視",但其實白人作為已有地位的族群所面臨的情況,同那些曾長期因種族或膚色而受到不公待遇的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族群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因而這些族群現在有權受到特別的司法保護。對這種做法持批評意見的人則提出,反歧視行動專案既構成了違憲的"反向歧視",而且也與《憲法》"不區分膚色"這一觀念背道而馳,違反了憑資格提升的原則,加重了種族不和,並且可能使這些專案所幫助的物件產生低人一等的感覺。
對於那些向反歧視行動專案提出挑戰的訴訟案,最高法院的裁決結果不一。在第一件主要案子中,即1978年的"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董事訴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法院面對的是配額制度問題。這個配額制度規定,在州立醫學院100個新生錄取名額中,有16個留給少數族群的申請人。在審理這個案件中代表主導裁決意見的路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法官,對最高法院的決定發揮了關鍵作用。鮑威爾代表自己和另外四位法官推翻了受到起訴的配額規定。他裁定,一切種族分類,無論涉及的是哪個種族,都必須受到嚴格的司法審核;無論多麼有力的理由, 都不能成為實行單純基於種族因素的錄取政策的根據。但是,鮑威爾和另外四位法官同時表示,一個州對學生成份多元化的關注,足以構成在錄取決定過程中將種族與其他因素一併考慮的根據。
在次年裁決的"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訴韋伯案"(Steelworkers v. Weber)中,最高法院的多數法官維持了一家公司及其工會共同做出的決定,即將某些職位中的50%分給少數族群的成員,直到少數族群的員工所占的百分比接近於少數族群在當地勞動力中所占的百分比。一個名叫布賴恩?韋伯(Brian Weber)的白人職工反對公司規定的這個配額,他的主要根據是,這種做法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的禁止就業歧視的規定。但是,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確定,該法律並不涉及公司為糾正當地過去的就業歧視後果而自願做出的種族配額的決定。
在伯格首席法官餘下的任期內,最高法院既肯定也廢止了多種反歧視行動措施。在1980年的"富利洛夫訴克盧茨尼克案"(Fullilove v. Klutznick)中,最高法院確定,國會通過的一項將聯邦公共工程經費的一個百分比專門留給少數族群企業承包的規定是合法的,法官們明確表示,聯邦一級的這種反歧視行動專案應該比類似的州和地方項目更受到司法上的尊重。在倫奎斯特擔任首席法官以後,各位法官最初仍然奉行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的這個立場,但是在1995年的"阿達蘭德建築公司訴佩納案"(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na)中,大多數法官認定,無論是聯邦專案還是州專案,都要受到同等嚴格的司法審核。
最高法院近年來對反歧視行動的反對態度也在選舉問題上反映出來。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後,在司法部的壓力下,有些州劃分出一些非洲裔美國人或西班牙語裔美國人占多數的選區;在這些選區中,少數族裔的候選人更有可能當選為國會議員。從一個意義上說,鑒於最高法院維持了1982年做出的對1965年《投票權法案》的各項修正案,它支持了這種特別選區的劃分。1982年的這些修正案規定,不但含有歧視意圖的州選舉法無效,而且如果州的選舉法具有分散少數族裔選民、使他們難以選出他們所中意的候選人的效果的話,亦將無效。但是,在對"肖訴亨特案"(Shaw v. Hunt)等一些案子的裁決中,最高法院允許白人選民對劃分這種所謂少數占多數的選區的做法提出挑戰。最高法院還以微弱多數裁定,如果主要是出於保證少數族裔候選人當選的種族目的來劃分選區,這種少數族裔占多數的選區是違憲的。
個人平等的信條
歷經司法裁決、國會立法、行政執行以及公眾態度的演變,美國社會已經穩步地轉向從法律上承認少數族群的權利。美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歷史上的弱勢族群長期被迫經受的最明顯的不平等。最高法院法官哈倫在1896年裁決"普萊西案"時提出的不同意見中曾經說過的一段鏗鏘有力的話,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現實:"從《憲法》角度來看,在法律面前,我們這個國家沒有高人一等、居主宰地位、掌握統治權的公民階層。這裏沒有等級制度。"
在美國,為結束對少數族群的歧視而進行的鬥爭主要是在法院、國會和州立法機構中進行。有兩個原因使這些努力取得成功。第一個原因,是法治及美國老百姓長期以來的信念,即個人或群體即使不同意法院或立法機構最後所確定的政策,公民也有義務服從這一政策。如果他們不同意某一政策或法律,他們會到立法機構進行遊說和到法院提起訴訟,而不是上街去橫衝直撞。
第二個原因,是體現在《憲法》、《獨立宣言》和立法與法院長期傳統中的美國的公民社會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權在法律下得到平等的保護。即使某個美國人因某些群體的膚色、生活習慣和語言等而不喜歡他們,但基於廣泛傳播的人人平等的信條,美國人必須與自己的偏見作鬥爭。儘管美國仍然沒有完全脫離歧視某些族群的歷史,但是,這個國家已經公開保證,要最終剷除種族偏見和其他各種遺留的偏見。
雖然這兩個信念 ─ 法治和人人平等 ─ 可能同美國的歷史經歷密切相關,但是,其基本原則可適用於普天下: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否則,國家就要生內亂。
相關讀物:
Charles A.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Oxford, 1987)
Richard F. Kluger, Simple Justice: 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 (Knopf, 1976)
J. Harvie Wilkinson, III, From Brown to Bakke (Oxford, 1979)
Deborah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Harvard, 1989)
Andrew Kull, The Color-Blind Constitution (Harvard, 1994)
---------------------
作者介紹:
廷斯利?亞伯勒(Tinsley E. Yarbrough)是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東卡羅來納大學政治學人文科學傑出教授。他撰寫過有關幾位法官的書,包括最高法院法官雨果?L?布萊克和同一姓名的祖孫兩位法官約翰?馬歇爾?哈倫。他最近的著作有:《倫奎斯特法院與憲法》(牛津,2000年)和《伯格法院:法官、裁決、業績》(ABC-CLIO,2001年)。
19楼
《論民主文集》(12)
文官統率軍隊
邁克爾?開羅 撰文
"即使在需要軍事力量時,在國內,……明智而謹慎的國人
也會時時刻刻對這個權力小心戒備和提防。"
─ 撒母耳?亞當斯
《獨立宣言》簽署人
****************
美國1789年以來較少介入持久的軍事行動。因此,美國公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國內事務上,對外交事務和國防只是偶爾關注。民意測驗一般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對外交政策事務比較漠不關心,唯有發生國際危機時,才會產生興趣。然而,美國當年建國的一個主要動機,如憲法所說,是為了"建立共同的國防" 。在美國《憲法》第一條第8款列舉的18項權力當中,有關軍事與對外政策事務的內容占三分之一。因此,《聯邦主義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又稱 The Federalist)最初有很多期都論及合眾國的國防需要,這並非偶然。
開國先賢在創立新的全國性的政府時懂得,建立起一個能夠正當保衛國家的政府是何等重要。要做到軍事與外交政策有效而統一,軍隊就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但是,他們同時認識到,如果對軍隊沒有足夠的控制,它有可能被用來奪取政權從而威脅民主制度。開國先賢對軍權可能被濫有著切實的擔憂,他們擔心,強大的行政權力久而久之會蛻化成獨裁或暴民政權。歷史告訴他們,這種濫權事例屢見不鮮。因此他們相信,需要在新憲法中表明,軍隊將被置於文職權力的管轄之下,以保衛民主制度。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28篇中寫道:
"拋開有關此事的其他一切論證不談,對那些要求針對和平時期的軍事建制設立更強硬規定的人們可以有這樣一個萬全的回答:提議建立的這個政府的全部權力,都將掌握在人民的代表的手中。對於公民社會給予人們的權益而言,這是根本的,而且歸根結底,也是惟一行之有效的保障。"
開國先賢們認識到,有必要有一支護民衛國的常備軍,但是他們認為,為了維護自由和防止濫權,必須十分小心警惕。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41篇中解釋道:
"提防外患,確保安全,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目標之一。……[但是]常備軍……是危險的,儘管同時可能又是必要的。最輕度地說,它帶來種種不便。嚴重地說,它可能造成致命的後果。無論如何,它都值得予以慎重對待和小心提防。一個明智的國家應該將所有這些給予綜合考慮;它一方面不可以魯莽地捨棄任何可能對它的安全至關重要的手段,同時又應該極為小心謹慎,減少依賴這種有可能威脅到自由的手段的需要及其危險。
這種謹慎的最明顯標誌體現在《憲法》提案中。由《憲法》形成並保護的聯邦本身,消滅了建立具有危險性的軍事力量的一切藉口。"
因此,《憲法》將組建和維持一支軍隊 ─ 也就是支付軍費 ─ 的責任歸於國會,以免總統權力過大。此外,正式宣戰的權力也被交給國會而不是行政部門,以避免做出魯莽和無法挽回的決定。但是,《憲法》同時指定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和各州民團的總司令,這就使得總統擁有充份的權力抵禦外敵進攻,保衛新生的國家。
然而,正如《憲法》中的許多原則那樣,文官統率軍隊的具體做法並沒有在《憲法》中得到明確規定。1789年的文官統率制度同今天的文官統率制度已經大不相同。其實,開國先賢從未設想過要有一批職業軍人,所以,他們不可能預見文官統率在今天的性質。因此,由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在美國的發展,既源於《憲法》規定,又是一種習慣與傳統的沿革。
公民-軍人的傳統
《憲法》本身並沒有論及建立常備軍隊的問題。開國先賢們並不熟悉職業兵役的概念。在他們看來,戰時服兵役是全體公民的天職。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固然是最著名的軍人兼政治家,但是,參加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許多代表,也都曾在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中擔過軍職。事實上,當時在人們的觀念中幾乎不存在文職與軍職人員的區別。
開國先賢的這一觀點可以從《憲法》第一條第6款中看出:
"參議員或眾議員不得在其當選任期內擔任合眾國政府在此期間添設或者增加薪奉的任何文職;在合眾國政府供職的人,不得在其任職期間擔任國會任何一院的議員。"
這一條款拒絕讓國會議員兼任行政或司法職務。它反映了憲法分權的基本原則,即政府的每一分支必須同其他分支涇渭分明。但是,在這一條款以及《憲法》的任何條款中,都沒有禁止參議員或眾議員受任軍事職務。開國先賢認為,議員是美國社會最有才能的人,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理所當然應在危機時刻擔任軍事指揮。事實上,當時把這一條款列入《憲法》的理由便是軍職不在此列。在開國先賢心目中,軍隊是非職業化的;從根本上說,軍隊由常備軍或民團組成,而唯有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時,才有常備軍。參加1787年制憲會議的代表埃爾布裏奇?格裏(Elbridge Gerry)曾做出這樣的解釋:"和平時期有常備軍是不符合共和制政府的原則的,對自由人民的各項自由是危險的,通常會變成破壞性的、建立專制制度的動力。"
在那時候,文官統率原則所體現的是這樣一種觀念:每一個合格的公民都有保衛國家和保衛自由的職責,必要時將參軍作戰。另外,也基於軍隊應該體現民主原則和鼓勵公民參與的觀念,開國先賢們認為,惟一合適的軍事力量就是官兵界線最小的民兵。
因此,開國先賢在獨立戰爭結束後,裁減了正規軍,依靠州裏的民團來捍衛西部疆界。這種裁減反映了美國民主制度對軍事建制和對軍隊功能的戒心,其部份根源在於殖民時期英國軍事統治的經歷。在整個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這種擔憂在美國政治和社會中紮根。美國這種抵制軍隊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加之地理位置的隔離,使文官統率軍隊的體制相沿至今。
在美國甫建之初居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也是造成這種對軍隊和軍事建制的反感 ─ 尤其是在和平時期 ─ 的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在17世紀40年代的克倫威爾(Cromwellian)時期,英國軍隊曾被用來鎮壓政治反對派,英國人對此的反應在18世紀仍然為人記憶猶新。而且,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一條主要導火線,就是1754-63年的法國-印第安人戰爭(French and Indian Wars)結束後,英國軍隊留駐美洲土地。殖民地居民反對這種做法,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應享有作為英國人的權利,而這種做法若在英國是不可接受的。這種小心提防的心態也貫穿於獨立戰爭本身。喬治?華盛頓將軍為了爭取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批准成立軍隊和提供軍費,必須向會議保證,決不利用軍隊來篡奪會議的權力。可見,即使在烽火連天之際,美國人對軍權仍然抱有戒心。
地理條件也對美國人看待軍隊的態度起了重要作用。在整個19世紀,廣闊浩瀚的兩大洋始終是北美大陸的屏障,而美國的鄰國對美國不構成嚴重威脅。在這種隔離狀態下,美國實際上不會受到來自歐亞兩洲的重大軍事威脅。美國豐富的天然資源也使它幾乎不必依賴外部世界。
所以,立國之初,有四個基本前提決定了美國人的文官統率觀念。第一,他們認為,龐大的軍事力量是對自由的威脅,這是由英國歷史和對殖民地的軍事佔領所至。第二,龐大的軍事力量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威脅。這個觀念與公民-軍人的理想以及那種生怕孳生出一個貴族或專制軍事階層的擔憂相關。第三,龐大的軍事力量是對經濟昌盛的威脅。維持龐大的常備軍會給當時這個新生國家的新興經濟造成沉重負擔。最後一點,龐大的軍事力量是對和平的威脅。開國先賢們持自由派的主張,即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於是,文官統率軍隊的制度在一系列歷史條件下發源,並且在傳統、習慣和信念的作用下,日益在美國的政治思想中紮下根來。
早期總統擔任軍事統帥
《憲法》關於總司令的條款規定,除其他職責外,"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總司令,並在州民團奉召為合眾國服役時任民團總司令"。這一條款成為貫穿美國歷史的基本原則,時刻要求以文職人員掌管軍事事務。基於參議員在戰時可以成為軍事將令的同一原則,《憲法》制定者決定由文職總統擔任軍隊總司令。這裏的關鍵在於,鑒於美國總統本人的所有職權都受到民主政體的制約,因此,他不太可能利用軍事指揮權調動軍隊去擴大總體行政權力。
開國先賢所期待的總統行使軍事職權的程度,可以從他們沒有對總統在戰場上親自指揮部隊的權力做出限制這一點得到說明。當時的意圖和預期是,總統可以而且應該在戰場上親自擔任軍事指揮。整個19世紀中的歷任總統都毫不猶豫地肩負了這個責任。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顯然開創了先例,他曾鎮壓了1799年賓夕法尼亞州農場主因反對政府徵稅而發動的一場暴動,即"威士忌酒反抗"(Whiskey Rebellion)。儘管暴動規模很小,波及地區有限,但是,華盛頓認為它是不折不扣的顛覆政府行為。華盛頓宣告,如果不平息反抗者,"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政府都會蕩然無存"。為表明聯邦的權威,華盛頓集合了一支堪與獨立戰爭時的全部軍力相比的軍事力量,親自率領這支軍隊出征賓夕法尼亞。
後來的總統效仿了華盛頓的先例。詹姆斯?麥迪森總統在1814年為抵禦英軍進犯而組織和策劃了的首都保衛戰,儘管未能奏效。在19世紀40年代的美墨戰爭(Mexican-American War)期間,詹姆斯?K?波爾克(James K. Polk)總統行使總司令的權力,親自指揮美軍對墨西哥軍隊作戰。儘管波爾克不是在戰場實地指揮,但他制定的戰略方針是軍隊作戰行動的依據。在整個19世紀,總統始終通過親自制定軍事戰略方針和參與純軍事性事務而指揮軍隊。其中以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最為突出。
林肯當時面臨著美國民主制度有史以來受到的最危險和最嚴重的威脅。面對著南方州的分離行動和聯邦的瓦解,林肯為保全國家而將總統的行政權力發揮到了極至。他將國會的一屆會議從1861年4月延期到7月。然後,他憑藉自己身為總司令的權力,召集民團,不經國會批准擴大了陸海軍,徵召志願兵入伍,不經國會撥款動用公款,中止"人身保護狀",並對南方邦聯實行了海軍封鎖。到了7月,他對國會說:
"別無選擇,只有動用政府(行政部門)的作戰權;因此,這是用武力抵抗以摧毀聯邦為目的的武力,從而保護聯邦。……這些措施,無論從嚴格意義上說是否合法,都是基於所看到的人民的要求、公眾的必需而毅然採取的;當時和現在都深信,國會定將爽快予以批准。……現在有一種觀點堅持認為,這個權力屬於國會而不屬於行政部門。但是《憲法》本身對於應由何方或何人來行使這一權力並無規定;而且,當時制訂這一規定純屬為了應付危急狀態,因此不能認為,立憲人的意圖是每當出現險情,在國會能夠聚集開會以前,只能聽之任之;國會的聚會本身就有可能因叛亂而無法進行,就像這次的情況一樣。……為保衛政府而動用作戰權力的職責落在總統身上,對此本總統深感遺憾。"
但是林肯行使的權力並不到此為止。1862年春季,林肯參加了對聯邦軍隊的指揮。他本人親自決定了作戰方案,並通過行政作戰命令指揮了部隊的行動。不過,林肯是最後一位如此直接介入制訂詳細軍事政策的總統。
林肯行使總司令權力的做法,更加確定了總統作為國家軍隊首領的地位。整個19世紀期如同18世紀一樣,政治才能與軍事才能沒有涇渭分明的界線。許多政治家擅長于軍事指揮,總統行使軍事職能也沒有造成什麼問題。這也許是因為,儘管林肯承擔起廣泛的權力,但是,各位總統都繼續尊重《憲法》對他們權力的整體制約。那個時期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政治-軍事等級:總統位居首位,身邊是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由他們直接向戰地的職業軍事指揮官發號施令。因此,政治職責和軍事職責仍然是相互交融的。總統往往原先就有過軍旅生涯,軍事將領也介入政治。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集軍事指揮與總統于一身的做法已經變得比較難以為繼。新式技術的興起、軍人專業化的潮流以及美國在國際舞臺上顯露頭角,使政治家同軍事指揮官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然而,在19世紀就確立下來的軍隊接受文官統率的牢固原則,即使在形式上有所變化,仍然作為傳統,在20世紀繼續發揚光大。
20世紀的新平衡
隨著20世紀到來的是一場大規模戰爭。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1912年當選總統時,美國的絕大部份注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時,威爾遜選擇讓美國保持中立。但是,美國的經濟利益和中立國權益所遭受的攻擊,促使威爾遜請求國會向德國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威爾遜未能爭取到參議院對國際聯盟條約的批准,美國因此陷於孤立。繼他之後的幾任總統,都遇到國會不願捲入國際事務的局面。在1929至1930年期間,國會通過了若干徵收高額關稅的法案,以"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達到高峰。這些關稅規定旨在保護美國經濟免受外來干預,使美國變得更加孤立。在1935、1936和1937年,國會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目的是保證不讓美國捲入另一場歐洲戰爭。
孤立主義在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執政期間達到頂峰。面對大蕭條的危機,羅斯福早在1935年就贊同實行中立,強調國內事務優於對外政策。直到30年代後期,羅斯福才開始看到美國參與歐洲事務的重要意義。
歷史的滑稽是,正是曾經試圖在國內事務領域對羅斯福"新政"的各項經濟改革政策施加掣肘的保守的最高法院,正式確立了總統在對外事務中的主角地位,加強了總統對軍隊的統率和指揮。在1936年審理"合眾國訴柯帝士-賴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urtiss-Wright Corporation)時,最高法院對總統處理國內事務與處理對外事務的許可權做出根本區分,闡明總統是"聯邦政府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唯一機關 ─ 這是一個不需要以國會行動為依據而行使的權力"。最高法院的論證是,《憲法》、歷史和現實的需要都使總統在對外事務上享有必然的權力。
當戰爭風雲密佈歐洲,國際問題佔據羅斯福政府的主要精力時,世界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技術革命使得任何一位總統都難以做到完全通曉用兵的真諦與戰略。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全球性的衝突。這些因素給在戰時與戰後由文職人員指導具體軍隊運作的觀念帶來了挑戰。然而在今天,文職人員,主要是總統及其工作班子以及國防部長,仍然牢固掌握著對國家軍隊的領導權。另外,基於《憲法》有關"財權"的規定,即由國會負責對軍隊的所有撥款,有意在這方面投入精力的國會議員能夠施加影響與控制。
1945年冷戰的開始標誌著美國孤立主義傳統的完全告終,它使美國走上了世界事務的領導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返回家園的軍人中,有許多人進入政府、學術界和商界工作,從而使軍界同商界以及社會其他各界彼此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繫。原先同美國社會多少有點隔絕的武裝力量,現在對社會有了大為活躍的參與。這個變化使得公眾和精英階層對軍界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曾經在19世紀占主導思潮的對軍界的擔心,在冷戰時代基本上轉化為對軍事力量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作用的理解和重視。
技術進步和美國對世界事務的參與,要求有新的政府機構來統率、組織、監督軍隊和軍事機構。1947年和1949年的《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規定成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從而加強了集中領導。國防部長屬於內閣級官員,直接向總統彙報,並且很快就成為軍事和文官指揮之間的紐帶。1958年的《國防部改組法案》(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加強了國防部長的權力,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60年代擔任此職期間發揮的強大影響,更增強了國防部長一職的權威。這些變化在新情況下幫助保持了總統在軍事事務上的權力。在整個冷戰時期,戰略權力的重心仍在於總統。行政部門通過白宮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和國防部長,掌握著對諸如軍力水準、武器採購與部署以及動用武力等事務的決定性權力。
由於美國軍方未能在越南戰爭中實現當時的作戰目標,職業軍隊的權威同文職當局相比進一步下降,再度造成許多美國人對軍事解決辦法和種種軍事手段的不信任,甚至軍方自身也對動用軍隊變得更為小心謹慎。自從70年代以來,許多軍事將領都不情願使用武力,他們提出,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為政治目的而有限動用武力將導致失敗。
他們的這種態度出於兩個原因。第一,越戰的失敗造成了一種"越戰後綜合症"。各任總統、軍方將領、國會以及公眾,都對靠武力實現美國的目標持懷疑態度。第二,國會伸張了它控制總統使用武力的權力;正是總統的動用武力權力將美國帶入了越南戰爭。1973年,國會推翻尼克森總統的否決,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War Powers Act)。這個法案的目的在於,限制總統不經國會同意就逕自出兵國外的權力。法案表明,它的目的是"實現《憲法》制訂者的本意……並且確保"在將美國武裝力量派往國外衝突時,"運用國會和總統的共同判斷"。該法案力圖通過要求總統同國會磋商並向國會報告,扭轉總統作戰權力增大的現象,並且說明了國會阻止總統使用武力的辦法。
儘管這是通過"戰爭權力法案"的本意,但是,由於國會不情願動用它,而且總統聲稱它違憲,因此這個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具有象徵意義。實際上,由於這項法案准許總統在國會同意之前出兵,它可能使總統動用武力的權力得到加強。
總的來說,在整個20世紀,無論是從總統還是從國會方面來說,文官統率軍隊的制度都在美國政府和社會中得到加強和進一步制度化。武器威力增加帶來的需要,進一步加速了文職官員更牢固指揮與統率軍隊的趨勢。
軍事顧問的限度
在美國進入新世紀之際,最可能出現的問題並不是職業軍人會不理睬或以任何方式抵制文官領導。相反,問題是文職領導人可能從背景和經驗上,都缺乏應付21世紀的種種複雜而危險的問題的專業技能。現在的挑戰是文職領導如何能夠有效地同職業軍人合作,以保證總統和他的工作班子得到有效決策所必需的專業技能和資訊。在美國歷史上,軍方對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影響,無論在性質還是程度都經歷了起伏變化。這種影響取決於若干因素,其中包括公眾的憂患意識以及經法律和傳統固定下來的軍隊結構與角色。美國軍隊自身的特色遠非是單一化的,不過,時至今日,軍方領袖在美國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最恰當地被形容為專家顧問。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期間的高層軍事指揮官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將軍曾作過說明:
"軍事顧問應該從交給他的方案中的軍事考慮出發,根據他自己對國家利益做出的無畏、公正、客觀的估計,在不受政府即時政策影響的情況下,提出自己過硬的專業意見。他應該將自己的意見局限於最重要的軍事領域。"
簡而言之,職業軍官應該是判斷如何最有效使用武力的專家,而在其他事務上聽從文職人員的意見。因此,美國《憲法》和美國傳統將軍人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限定在職業性和執行手段的範疇。
在20世紀和21世紀交接之際,呈現給美國軍方領導人的使命,不是決定應該在何時何地進行戰爭;他們所面對的是狹窄得多的問題:在某個具體情況下,為某一具體的戰略目的,軍方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最有效?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在1983年並沒有就美國軍隊是否應該進入格林伍德平定危機徵詢軍方意見,而是問他們將如何完成這個使命。布希總統和克林頓總統也沒有詢問軍事指揮官是否應該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或是否應該保護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人免遭塞爾維亞人的欺淩。他們只是詢問如何能迅速達到這些目標而又將傷亡減至最低限度。因此,習慣、傳統和法律共同將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牢牢地確立在美國的政治和社會中。
對於那些正在努力解決新興民主制度的種種難題的國家來說,美國的經驗可能有寶貴的參考價值。最明顯的難題,也許就是軍事指揮官有奪取政權之虞。有兩條重要的原則,可以使文官統率制度得到加強。第一,從憲法上奠定文官控制軍隊的基礎將對新興民主國家有益。美國《憲法》在這一點上儘管存在模糊之處,但是將軍權分別交給了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以防止濫用權力。而且,《憲法》還明確規定由總統這一民選產生的文職領導人擔任武裝力量總司令。這裏的關鍵在於,總統的各項權力從整體上是有界定、有限制的,而且國會、各級法院以及選民,都有實在的權力。因此,總統對軍隊的指揮權不會延伸為對其他方面的指揮權。總統的主要身份是文職官員這一點,從美國歷史中得到體現。只有四位總統,即華盛頓、傑克遜(Jackson)、格蘭特(Grant)、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在當總統之前有過相當可觀的軍旅生涯。他們每一位都很明白,軍事職能和政治職能必須明確區分。艾森豪威爾將軍是如此嚴格地奉行這一原則,以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歐洲盟軍作戰指揮時,不參加選舉投票。
第二條關鍵性的原則是,軍人必須扮演職業性而非決策性的角色。艾森豪威爾身在行伍時拒絕投票的做法說明,他深信軍事上的決策不應被政治上的決策所干擾。軍事將領不應捲入政治決策過程。他們提供的軍事意見,應該是為了達到政治決策者的目標,以及說明在軍事上有多大克敵制勝的把握。至於是否應該選擇軍事手段,則應由政治領導人決斷。
實行這第二條原則比實現《憲法》保障要困難得多。《憲法》就軍事和政治領導的適當分權做出具體成文規定是卓越的第一步,但是,讓軍方確信它的這種從屬角色並非輕而易舉。文官統率軍隊所碰到的主要障礙,通常關係到崇尚戎武的文化。改變這種文化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這是要軍隊接受文職領導所必須的。它需要通過時間和教育來實現。老式的軍方領導人如果不信任文職領導,就應該由願意同文職領導合作並為之效力的新領導人所取代。顯然,如果文職領導是民選的,他們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有助於他們領導軍隊。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但不會比建立良好的民主政府更艱巨。應該明確這樣一點:一支將自己視為民主社會一份子的軍隊,只會更強大,而不會變得衰弱,因為它的行動會更能反映出它所服務的人民的最大願望。
相關讀物:
Kenneth C. Allard, Command, Control, and the Common Defen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eter Douglas Feaver, Guarding the Guardians: Civilian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rew J. Goodpast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Vintage Books, 1964)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Free Press, 1980)
Burton M. Sapin and Richard C. Snyder.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oubleday, 1954)
Adam Yarmolinsky,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Perennial Library, 1973)
---------------------
作者介紹:
邁克爾?開羅(Michael F. Cairo)於1999年獲佛吉尼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在弗吉尼亞州大學、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目前在威斯康星大學斯蒂文斯波恩特分校任教。他的研究重點是美國對外政策及對外政策制定過程。
--------------------------------------------------------------
14楼
打倒军国主义!![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em29]
11楼
原文由 [B]yy[/B] 发表: 飞鸿...早啊!! 辛苦啦....................[em43] [em36] [em39] [em43]
发表于:2004-08-17 00:45只看该作者
20楼
[em12]
不是看你怎样想、怎样说,而是看你怎样做!
发表于:2004-08-17 01:01只看该作者
22楼
[em58]
发表于:2004-08-17 02:22只看该作者
6楼
[em64] [em72]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发表于:2004-08-17 02:33只看该作者
21楼
飞鸿DD最近回来好象大字报式的帖子多了啊,红字加大字,最近情绪好象比较激动?呵呵
不用太在意,平和的心态很重要,我记得这就是我以前印象中的你
[em80] [em2]
发表于:2004-08-17 02:41只看该作者
26楼
不要管那些S人S事。贴什么上来,自己知就好了,这里比以前差劲多了。
韬客社区www.talkfx.co